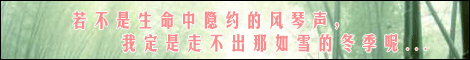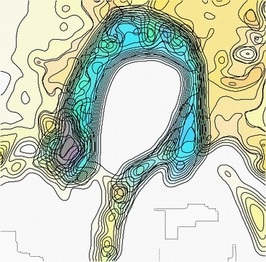








去年十二月,我去无锡参加中国石油文协四届四次会议。我到会最晚,忽然地想找一个伴儿同住。
我就问到会的女作家有谁愿和我同住?服务员说女代表只有四位,从四川来的两位一间,还剩一位从北京来的叫冯敬兰。我心里高兴,因为冯敬兰大姐我早就认识呀!我脑海里的冯大姐高高的额头,庸容高贵,手里织着毛活儿。
我就让服务员去问冯大姐欢迎不欢迎我的加入。不一会儿,话就传回来了:冯敬兰非常欢迎你和她同住。
不知道为什么,往冯大姐大姐的房间走时,心里的暧融融的。
冯大姐出来接我。又拿箱子又拿包。
落坐后,让我惊奇的不仅是冯大姐的热情,更有她又拿在手中的毛线活儿。那毛线团似乎是粉红色的,让人不能不感觉温馨。冯敬兰大姐还是那样又高又胖,身着粉红色宽松毛衣,浑身都充满了女人味儿。
那房间的空气中因为有了她,仿佛有一个粉红粉白的大气场,让人感觉温馨放松,那感觉真是太神奇了。
冯大姐挂在那的外衣是一件皮夹克,却也是那种宽松式样,皮子一看便知是那种极细极柔的一种,仿佛那皮可丝绸般揉在手里,变小了,变没了。
她说她也正想找一个伴一起住,免得孤独寂寞。我们都高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一时间,我感觉这的房间也变得暧融融的。
冯大姐还特意叮嘱我:这一路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同住,好吗?您知道我一个人睡不好觉,正发愁呢!
冯大姐一边织毛衣一边给我侃大山.说到她的父亲自杀,说到她小时见过父亲的灵魂,说到母亲到楼房来住的不适应,说着说着,我的忽然感自己头脑发昏意识出现了阵阵恍惚.她讲的一一切都带着一种似曾相似的大气场,仿佛她曾经给我讲过这些,可是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是我更不明白的是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冯大姐了,她讲的许多事情是近年发生的,我怎么可能听过呢?但是甩甩头,仍是甩不去那种似曾相听的大气场.
我很多年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冯大姐。那是在中国石油的大楼里,那是中午休息时,别人都在打磕睡,她却在那里一边织着毛线活儿一边和我小声说话儿。
这一次她仍是一边织着毛活儿一边和我小声说话儿。
我进中国石油比冯大姐晚好多年。我进来后听文联的人说过:冯大姐是83年任文联主席的徐光耀从华北油田挖掘出的作家。徐光耀是我所喜爱的《小兵张嘎》的作家。是三十四岁早逝的作家宋克力的一句“遗言”促使原本只是一个医生的冯姐深入女子钻井队写出了《夏日辉煌》。八九年评论家曾镇南评价《夏日辉煌》时说,些作品堪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同样厚重。冯大姐还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身后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故事。
而冯大姐给我留下深刻影响,还缘于冯大姐毅然告过一个敢于SR她的大作家,一位不知名的文学班学员.我感觉她真的很有个性.
我心里惊奇,难道这么多年她就这么一路织来,织到现在吗?想想那该织多少毛活呀。那织过的毛线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转呀!
果然不一会,冯敬兰大姐就说:毛竹我给你织一件毛衣,好吗?居然有一点乞求我的味道。似乎是求我接爱这份真情。这让我好感动。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妈妈,还没有其它人这样问过我呢。我的拒绝不是真心的,因为我怕这份友谊承受不起。因为享受那一针一线织出的毛衣的温暧,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上是多么大的一种奢侈?而妈妈从青海织好寄给我的毛衣我总舍不得穿,那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珍藏。
而我的生活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日子,只是持续没有这么长久。那是我刚上初中时。我最擅长是钩花,钩得每一个朋友每一位亲戚的家里都有我毛竹钩的一块。或是桌布或是台布,或是窗帘或是茶几盖,或是一件毛衣,或是一双婴儿小鞋。或是一个小女孩子的裙子,或是一个小男孩子的书包,或是一个淑女小包或是一个阿姨的凉帽。让妈妈买线都买不及。我用的线是各种各样的,什么羊毛线、棉线、地毯线,真可谓五花八门。不似冯大姐这么单纯。
织毛活儿,在我看来,对于能写那么好文章的作家冯敬兰来说,真是难得!这都什么时代了!我周围的女人大多不织毛活不用缝纫机了。连我的妈妈,曾经的缝纫高手,现在都不用缝纫机了。
冯大姐说她现在已经处在一种半退修的状态,每天很晚才起床,收拾一会家就中午了。下午在博客上写点东西,晚上就一边织毛线活儿一边看"寒剧"。看累了起来浇浇花,喂喂猫。日子过得充实而悠闲。
难怪有人如此评价她:冯大姐写得字好、文章写得好、画画得好、手工做的好。
难怪有人如此评价她:"冯敬兰是个好作家,好医生,好母亲和好妻子。"
我不明白在别人的评价中一个女人怎么可占有这么多的“好”。
我和许多人一样,总听人提起韩剧,但是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总感觉没有时间进入。可是冯大姐说起韩剧,竟如数家珍,什么《加油金顺》、《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爱情是什么》等等,并说光《加油金顺》她就看过三遍。冯大姐说好看,让我也有了一种某年某月某天一睹为快的冲动,把韩剧扫荡一遍。我让她到时给我推荐一些好韩剧,她说没问题.
冯姐姐说她最近写的文章,写台湾的标题是“那个比大陆更加中国的地方”写西藏的标题是“到世界最高的地方去呼吸”,给我的感觉都是很灵气的。
她又说起她的父亲去世后的情景,说她见过父亲的灵魂。她说这些话让我有些儿昏乎。因为许多的话和多年前我见她时,她对说的话好像一模一样。我恍惚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是多年前她说的话我都记得?还是她说的话我梦见过?还是她的书我看过?于是这些话如同从我的恍惚中浮出,熟悉中带出一种怪异的美。
她还说起好多她女儿的事情,女儿的婚姻观,女儿的爱情故事,女儿的男朋友。
她还说起女儿给她的感触写的文章《你是否相信陌生人?》在网上引起的热潮和轰动。
冯大姐说写这文章是源于女儿对陌生人的信任:有一次女儿在超市排队等待付款,前面一个陌生阿姨忘了带钱,女儿马上给阿姨借五十元。阿姨要了女儿的地址。多少天后,冯大姐收到了这笔从陌生地方寄来的五十元钱。冯大姐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讲了那个故事。冯大姐问女儿:有电视剧名叫《千万别相信陌生人》,可是你倒好偏要相信陌生人,万一人家不给你还钱呢?女儿说:我为什么就不能相信陌生人呢?我有直感,她会还,实事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再说,就算是不还,我也愿意帮助她。每当她回想这件事情时,她会有种来自内心的感动。就是负我,每当她想如法炮制时,她会有种来自内心的疚痛。下一次遇到帮助她的人她或许就不会不还钱了。
冯大姐还讲了许多女儿的事情:女儿坐出租车把钱包丢在车上了,出租车司机发现后一个店一个店一个地找着,给女儿送回来了,女儿顺手就从钱包中抽出一张大团结塞给出租车司机,出租司机不要,可是女儿硬是塞给了出租司机。冯大姐问女儿:为何要给那么多?五十元不行吗?女儿说:我只是想给做好事的司机一种信心,一种支持,一种鼓励。
冯大姐说女儿总是给报厅的售报人一百元,然后随意拿报刊。总是问:“钱不够了吧?”够!还多呢!”“不够了吧?”“还有十元”“那我再放下一百元”。女儿从来不算不数不对帐,绝对地相信陌生人。冯大姐有一天忍不住问:“你为什么总是相信陌生人?”女儿说:“我为什么不能总是相信陌生人?”女儿停停说“因为您看到了,他们实是值得我相信的呀!你说不是吗?”
冯大姐讲的女儿爱情故事也似她手中织的毛线团一般缓缓拉开,温馨而又感人。充满了生活气息。
冯大姐眼睛忽然变得深邃冷静,深不可测.如同变成了神秘的阴暗的"海沟".她说出对我有许多的疑问,关于我她可能是听到太多,也不掩饰,直指要害,一一发问,机关枪一般"嘟嘟嘟"地扫射我。她还给我讲了许多过去石油文联石油文协事情的内幕。真可谓入木三分.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冯大姐请我吃饭,说自己很能喝白酒,能喝多少,不知道,反正是从来没有醉过.冯姐对事物的洞察也和她的酒量一般深不可测.
我感觉冯大姐真的像一个亲姐姐,让我轻松而又放松。
当晚不论是经常失眠的她还是夜猫子我,都早早地睡了,都睡了一个粉红色暖乎乎热乎乎昏乎乎的觉.冯姐醒来说:"奇怪,有了你我睡得真好!"我也说"奇怪,有您做伴,我这么早就酣然入睡,一觉睡到大天明!"仿佛我们相互都成了对方的"催眠物",故而更加相互珍惜.
她热情地邀请我回京后到她家去看看,仿佛如果我去,她在家也能睡得更好一般。而我对她的生活、她的创作、她的网站、她的房子、她的盆花、她的猫咪、她的女儿、她的丈夫,真的很好奇,当时就决定如果回京,一定抽空去冯大姐家看看。
回京后,终于有一天,我在李玉真两口,肖复华妻子的陪伴下去了坐落于tty冯大姐的家。
到她家后我发现她的家很大,如果客厅中多一个屏风,感觉会更适合冯大姐。
我们先各个房间视察了一番。我发现了书架上罢放着一个着樱花金线图案桃色和服的温馨日本的女人木贴图,真是太美了!那日本女人短短的头发,脸上丰腴如桃、脖子是一个灵气的桃尖尖儿插在和服领子中。和服中出露的肌肤十分白晰柔美,整个图案的造型精美别致,桃色隐动,金线飘逸,高贵富丽,整个图案的气氛更是和谐柔美。我一眼就看上了。
全部房子参观完,我说:冯大姐,你知道我看上您家什么吗?冯大姐问是什么?我说:那个日本女人木贴图
没想到冯姐马上表态要把它送我。一时间我的心里又充满了温馨。我怎忍夺人爱,可是那图我实在是太喜欢了。让我身不由已极想拥有。
冯姐姐很快拿来那日本女人木贴图,并在后题上了字:
送给毛竹妹妹,祝新春愉快!
冯敬兰大姐。
冯姐交给我时说:知道这是从哪里带回来的吗?从日本带回来的。
我觉得这个小礼物真是太珍贵了。
我说:冯姐,告诉您一个秘密:你知道吗?知道我为何喜欢这个日本女人木贴图吗?这个日本女人的神韵很像您!
我的心里有个感觉终于清晰,冯大姐给我的气场感觉就是这若白若粉樱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着樱花色和服女人给我的感觉。
冯姐一怔,马上恢复了那种洞察一切冷眼向阳看世界的深邃,她反对道:从没有人这样说过。冯姐又变得冷峻深邃,身上出现了拒人千里的傲气.她说:"毛竹你太会恭维人了?"我一怔,心想,什么您说什么?我还会恭维人?您都退休了我凭何要恭维您呢?您给了我什么我要恭维您呢?我想从您这得到什么我要恭维您呢?
一下子,我也变得深窆严峻起来.我说:"冯姐,您别不自信!我是一个感觉多少说多少的人."
我强调:是神似韵似,而不是形似貌似!我把木贴图转向三个伴儿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说:“我的直感是经得起时间的,十年或是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以后,您可能还会记得毛竹的评价,您终会承认这个胖胖的头发短短的日本女人的神韵真的真的真的很像您!”
我这么一说,李玉真两口和肖嫂已经看出那种神似韵似,已经开始点头认同,已经开始惊叹起来.而冯大姐也似蓦然间发现了自己一般,惊异无比,震惊无比。仿佛她从来就不认识自己。冯敬兰大姐眼中忽然出现的拒人千里的冷峻渐渐消失了,蓦然冰封万里的河崖冰块渐渐消融了.气氛又趋向温馨.
我再看温馨的冯大姐,再看手中那个日本女人,越发觉得自己的那一感觉真的太神奇了。我的心在这一瞬间倏然充满了灵异。我对自己的不经意出口的评论也惊异无比。为什么我总有这种比我的思想还快的见解从我的口中逃出?抓都抓不住,拽都拽不回来?
“注其神而忘乎其形”“注其内而忘乎其外”,我常常的真的是“涉江而过,芙蓉千朵,诗也简单,心也简单”。可是我的瞬间感觉真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别说让别人让我自己都想不到。别说让别人让我自己都惊叹不已.
我说:冯大姐,看来您还不了解您自己的神韵。这也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我心想,冯大姐你让人想起唐代的胖美人,日本的胖妇人。
您虽然不会让人想起:“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的诗句,但是却让人想起“人面转身家中去,桃花依然笑春风”这样的诗句。
望着冯姐又开始织毛活儿,我忽然地想,冯姐手中的毛线,这么多年,一路织来,可绕地球多少圈?这一瞬我感觉冯姐飘浮了起来,身下的云,身下的山,身下的水,都是她堆下来的毛线。我莫名其妙地不合时宜想起毛老人家的诗:“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江河。”
回家时,冯大姐派她的先生开包面车送我回家。冯的夫在某医院负责。
回来后我上网觅寻冯姐的稿子,发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贴近生活的。贴近家庭生活,贴近社会生活,贴近石油生活,贴近石油社会。
有一天,现代司机报的会计吴永琴说起冯敬兰使劲笑.他说:那一次冯姐到了敦煌,听说当地人都满地挖锁阳.锁阳是壮阳的.冯姐说:"挖!挖!让他们挖!让他们吃!让那些骚男人晚上都睡不成觉!整夜整夜辗转反侧!"
我俩笑,笑成了一团花,我又感觉到了冯姐姐身上粉红粉白温馨宽松的大气场。
链接一
冯敬兰
河北蔚县人。1975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医疗专业,1991年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1968年赴北大荒插队务农,后历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团农工、小学教师、文书,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卫生院医生,华北油田采油四厂医生、宣传部干事,高级政工师。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中国石油文联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
链接二:东北博客
|
我们的故事之八十——我从哪里来
作者贾宏图 |
|
北京的知青大概有两伙人,有来自胡同里的,有来自大院的。来自胡同的多数为平民子弟,当然胡同深处也有些旧王府和达官贵人的私宅,后来住进些高官和名人。来自大院的一般都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什么总参大院、总政大院、海军大院、空军大院的。大院的知青返城比较早,当兵了、上学了,这方面他们的门路多。兵团也算是部队系列,反正家长总能找到门路。苦了那帮“胡同串子”,家长都是寻常百姓,也想让孩子早点儿回来,可干没招儿,就靠孩子自己熬了。
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冯敬兰自称是个“胡同串子”,小时候住在人民大会堂西边的一条胡同里,虽然也说着一口纯正得和皇族一样的京腔,但过的却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日子。先辈也曾吃香过,后来家道衰落,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父亲也算是世家子弟,祖上先后有二十多人考取过功名,一位高祖是道光丙申年的武进士,后为道光的御前待卫。父亲本来已经当上了察哈尔解放区一个非党的副区长,可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自杀了。那一年,敬兰只有六岁。没享着一天福,后来她却因此受株连,没少遭罪。
还好,“胡同串子”冯敬兰考取了北京当时最好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那是北京的“皇族学校”——共和国元勋的女儿基本都在这个学校读书。平民子弟都是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才进入这所学校,但他们被歧视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时,敬兰是初三的学生,却受到那些当然的“革命可靠接班人”的批判,罪名是“作文总当范文,太清高”、“偷看《参考消息》”、“仇视干部子弟”,最严重的是她竟公开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她在辩论会上说:“什么是混蛋?如果说,有点儿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混蛋,那么我们都是混蛋!”当然,只是同学们互相批判,北师大女附中也不会出名,冯敬兰后来在一篇纪念母校的文章中说——“八月初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48岁的女校长经历了一天的非人折磨后惨死。当年最好的女子中学,精英式教育,女校长最爱、最呵护的革命后代,来自为共和国流血奋斗的家庭,她们制造了北京乃至全国最早、最骇人听闻的惨案。”
也许为了摆脱心灵的伤痛,1968年6月,冯敬兰下乡来到了宝清县南横林子的852农场(20团)6营4连当农工。一个月后,队里安排她当气象员兼出纳,主要工作是每天四次记录风向、风速、湿度、温度,到月底时给大家发工资。敬兰回忆,当时我找连里领导说:“我不行!我是初中生,出身不好,不是团员。我们同学中有不少出身好,又是高中生的,怎么让我‘脱产’?再说,我还没过劳动关呢!”指导员说:“你太单薄了。等你长大一点壮一点,再过劳动关也不晚!”“那时,我身高168厘米,体重47公斤。一个月后,连里又安排我到连里的小学当老师。看到战友们下地回来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我觉得自己不下地干活,好像做了亏心事。当时我负责教六年级和一年级,一年级的30个学生,是我挨门挨户招来的,大的12岁,小的才5岁。要命的是当时没有课本,每天教什么,全凭自己想。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中挑选短文,再自编些应用题,算作语文算术两门课。上课时,我给一年级讲课,六年级抿着嘴看,好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指导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小孩就瞪大眼睛瞧着我。我看到他们神秘地交头接耳,于是拉了一个长声问:“你们在说什么?”小孩转过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你的外号叫‘麻杆儿’。”课堂上一片哄笑。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笑脸。 第二年春天,连里召开大会宣布营里任命的干部。冯敬兰一听,自己还是小学校的老师,她立刻跳到指导员面前大吵大闹。连里实在没办法,让她到了农工排。敬兰说:“当时我就想让别人看一看,我也是能吃苦的,什么活我都能干,我和你们一样也是革命的。现在一想起当年连里干部对我的照顾,我的眼泪不禁从眼眶中流出,涌上心头的是感谢、感激和感恩——谢谢你们对一个18岁女孩子不懂事的宽宥!”后来,因为冯敬兰的文字能力强,被抽到团里参加工作组,派到种兽站搞“一打三反”。在那里,她认识了浪漫的诗人郭小林和他漂亮的恋人、当地姑娘小杨,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次又是小林介绍我结识了京城才女冯敬兰。
工作组完成任务后,冯敬兰被安排到团供应站当了文书,尽管全团都知道她是个难得的才女,可连入团都很难。指导员拿着她的外调材料对她说:“你妈和你说过没有,你爸是畏罪自杀的,你家是和共产党有仇恨的!”她含着眼泪向指导员说明父亲死亡的真实情况,可组织上还是把她划到了另类。冯敬兰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泥泞的路上跋涉,想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热心为全连职工家属服务,取暖期到了,她跟着车到煤矿为各家拉煤,顶着“大烟泡”为各家送布票。连里搞基建,她晚上忙自己的活,白天在工地上抬砖、拉石头。连里修水利时,她和大家一起到工地,挑淤泥,脸都冻肿了。1972年,在她22岁时终于入了团。这时冯敬兰看到了自己人生路上的一线曙光。紧接着,在1973年的推荐大学生中,她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文革粉碎了一代中学生的大学梦,可这个重点中学的学生并没放弃自己的理想。在全连推荐时,冯敬兰在三个侯选人中得票最多。可到了团里被卡了下来,管事的组织股长说,冯敬兰的政治表现有问题。其实问题出在她曾给团领导写过信,反映一些现役军人的家属飞扬跋扈,主要批评了这位股长的夫人。结果这封信又转到了这位股长手里,这回他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在他的压力下,没办法,连里又进行一次推荐投票。这之前,已经有人散布,冯敬兰的父亲被人民政府镇压而死。结果敬兰的票又掉下来了。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冯敬兰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她到团里***,揭露个别人的阴谋,团里派人来调查,又组织重新投票推荐,这次冯敬兰还是得票最多,团党委批准冯敬兰上学。可惜经过这一折腾,只剩下个齐齐哈尔医士学校的名额了。作为北京重点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再去读一个中专,实在有点委屈。可她还是去了,因为这是正义的胜利。
在那个并不著名的学校里,冯敬兰过了四年平静的学习生活。那是个不平静的年代,文革的余波还时常在学校掀起波浪。冯敬兰还扮演着“反潮流”的角色,学生们要批判老师,她坚决反对,因为她目睹过自己的校长死在大批判中。学生要求学校废除考试,她坚决维护必要的考试。她在所有的考试中都是名列前茅,连年是三好学生。在学校期间,冯敬兰和依安县的民办教师、她的同学王守先相恋并结为连理。他是一个下放农村的“右派”的儿子,兄弟六人,家里一贫如洗。下乡后母亲一再告诫冯敬兰:搞对象不要找排行老大的,不要找农村人,不要找东北人!这几条她全违反了。冯敬兰说:“当时我可能正处于逆反的青春期,和我妈就是对着干。为此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整个命运都改变了。后来,因为我,老王一家也改变了命运。”
因为嫁给老王,冯敬兰毕业时不可能回北京,连留校或分到一个比较好的城市的可能都没有。1975年7月,她和老王到条件还不如南横林子的逊克县逊河公社卫生院报到了。这个黑龙江畔极小的村镇很有名气,因为在这儿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就是因为捞被逊河水冲走的电线杆而牺牲的。他们和老乡的感情比金训华还深,因为这对夫妻医生为老乡们的生命和健康起早贪晚、随叫随到。他们医术高又心地善良,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们还是走了,因为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把她一生都扔在这僻远的山乡。
敬兰能走出逊克,是因为她当年的同桌、和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叶维丽(现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那时,绝大多数北京知青都返城了,让自己如此有才华的老同学留在北大荒,叶维丽心里不安!正好她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母亲和华北油田的领导很熟悉,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母亲找了一位领导,那位可敬的油田总指挥写了条子,就这样冯敬兰和老王于1978年2月南下到了任丘,成了燕翎一个基层油田卫生所的医生。说实在的,那里的条件远不如逊河卫生院,只有一顶帐蓬,简单的设备,加上他们两个人。老王天天和她吵架,闹着要回逊克。那时女儿在北京的母亲家,他们饭都不想做。就是做饭,吃完后谁洗碗,要下棋决定,当然经常是老王代劳了。实在没事干,老王和工人去打篮球。冯敬兰无聊中拿起笔,她想当年我作文不错,不信就不能写点出东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次参加在任丘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她写了一篇反映知识分子经历的小说,晚上十点多钟河北文联主席、老作家徐光耀来找她说:“读了你的小说,我睡不着觉了。看来这一趟我没有白来!”后来这篇名为《路这样走过》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83年第三期文学季刊《长城》上。这位曾写过电影《小兵张嘎》的老作家,从一篇中学生作文中发现了铁凝的才华,这次又从众多油田作者中发现了一位潜力丰厚的女作家。后来,冯敬兰一发而不可收,佳作不断,在河北和全国石油系统都得了最高的文学奖。就这样,她加入中国作协、进鲁迅文学院学习、到北师大读研究生、其作品开研讨会就顺理成章了。在讨论会上,著名评论家唐因说:“冯敬兰的作品是一流的,我说的不是指她的所有作品,我指的是她的文学素质和文学品格。她有这样一些优点:对生活敏锐的感受,深沉的思考,有一种真诚的激情和一种广大的柔情。”
和那些文艺界的女名人一有名就离婚的惯例不同,冯敬兰和老王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老王在一家医院当门诊部主任,冯敬兰通过自己的影响,把他的父母和兄弟都调到油田安排了生活和工作。
当然,最让老知青们佩服的是她对自己女儿的培养。这个网名叫“燕七”的姑娘,本来冯敬兰想安排她到母校借读,而且她的考试成绩斐然。可因为拿不起赞助费,又没有北京户口,她不能入学。敬兰曾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给知青子女平等的待遇。1988年政府出台了可以为北京知青子女落户口的政策。当冯敬兰在西城区公安局为女儿落上户口那天,她竟在街上泪流满面。后来,“燕七”名正言顺地考进了著名的北京四中。四中毕业后,她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新闻研究所读研究生。这个特立独行的姑娘,读高中时就自己打工挣钱在外租房子住,大学还没毕业就自己挣钱买了房子。现在这位《中国青年报》的“白领”,在网上相当有名气,许多人是通过“燕七”知道她的母亲冯敬兰的。
应该说,中国石油界文坛的领军人物冯敬兰(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石油文联主持工作的秘书长)著作等身,知名度相当可以。但是她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她在网络(搜狐博客:“看了又看”)上发表的那些特别有人文情怀的散文。比如她写女儿“燕七”的那篇《你是否相信陌生人》,还有《春游台湾——那个更“中国”的地方》。那篇《有感于林晓霖代父谢罪》就更火了(也是北师大毕业的林晓霖看了老同学章诒和的散文集《往事并不如烟》,马上给她打电话说,我的父亲对不起你的父亲,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挨整的知识分子。两位校友都泪流满面。就此,冯敬兰发了一番感慨。)。还有那篇《最后一课》(关于校长之死)像铁锤在敲着我的心,我还想抄录下来,让一代人勿忘——
“她们是谁?至今没有一个参与者站出来,说明真相,公开道歉。她们忘了吗?她们已经原谅了自己?是的。她们在努力忘却。她们用‘我当时是孩子,文革的责任凭什么要我承担?’来抵御社会良心的拷问,原谅自己。同时他们也念念不忘并放大着文革中父母被迫害给他们带来的伤痛。这是奇怪的一段历史啊!
校长之死虽然与我无关,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到耻辱。女校长死于自己女学生的手下,是我们一代人的罪恶和羞耻。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女校长。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的心理,已是我们生命中的毒素。只有清除它们,我们的生命才更加健康;只有用理解和温暖去善待别人,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更美丽。”
我在另一篇知青故事中曾说,如果每一个知青在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在经历许多苦难之后,能敬畏大自然,能爱护大自然,能养成惜天悯人的情怀,那么我们就不枉为北大荒人。现在我要说,冯敬兰作为一个北大荒老知青,在饱经人生风雨后,能透彻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这一代人,并毫不迟疑揭开我们的伤疤,我以为她是知青中的智者。她的人文情怀,是我们的共同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