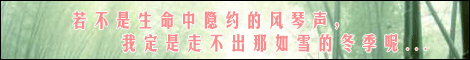惊艳!张爱玲菜单
像一只红嘴绿鹦哥般寻味上海
她对于鱼虾之类完全不会吃,无肉不欢;她同老年人一样偏爱“甜的烂的”,幼年向往一切小孩不能消化的糯米点心;虽然被称作“天才”,她的童年理想却是长大了在一家牛肉庄找个事做,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当她已经像一只红嘴绿鹦哥般调理自己的时候,她的男人连生煎馒头和肉馒头也分不清爽;晚年侨居国外,她的美食文章里随处可以闻见上海味道。
张爱玲这样一个感官敏锐的女人,才会拥有活色生香的生活以及文字。年岁渐长,当你渐渐淡忘她笔下那些男男女女的小事情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味蕾却不见迟钝——把那张用来亲吻的嘴腾出来后,终于发现那一口老鸭汤才是真真切切地暖在心口,而且谁也抢不走。
福1088:20道小菜成就一桌张爱玲全席
难的是凑成一席,即如何把这些零散在字里行间的“虱子”们逐一捉将出来,再按“前菜热菜汤主食点心甜品”之顺序,分门别类地绣成一袭华美的袍……把人家一生吃过的东西压缩到一顿晚饭里。——沈宏非
去年9月30日(张爱玲生日),老洋房餐厅“福1088”的老板请来了沈宏非等人,热热络络地吃了一顿张爱玲的“软饭”。从苏州赶来的叶放当晚所贡献之黄酒,名字偏偏就叫“海上花开”。“张爱玲男朋友”雅称的陈子善携其珍藏的张著数十册赴宴(包括部分初版书,有一本还有张爱玲的亲笔签名),而且还以“未亡人”的身份在其右侧空了一个座位给爱玲。小菜还没端上来,酸味倒是满满一屋子了。
那份菜单按“前菜热菜汤主食点心甜品”之顺序,共有20道,分别取了“相见欢”、“倾城之恋”等作品名,几乎覆盖了张爱玲的一生。
“合肥丸子”是早期的家常菜。张家小弟张子静记得最牢:“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做法也不难。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再把调好的肉糜放进去捏拢好,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饭团放蛋汁里滚一滚,投入油锅里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
福1088的招牌菜熏鱼恰恰是张的心头爱。她幼时跟私塾先生念书,把《孟子》里的“大王事獯于”记成“大王嗜熏鱼”。按照心理学的讲法,张爱玲是爱极了熏鱼才有了这样的口误。
生煎馒头与胡兰成相关。胡自己也在《今生今世之民国女子》中说:“一次瘪三抢她手里的小馒头,一半落地,一半她仍拿了回来。”喔唷,连“生煎馒头”也不懂,难怪胡兰成被讲成汪伪政权里最不会吃的一个。
张爱玲吃面的习惯倒是和如今的上海MM有得一拼。哪怕是杭州楼外楼的螃蟹面,也还是“吃掉浇头,把汤泌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有点造孽”。
寻踪提示:
福1088位于镇宁路愚园路口,是福1039的老板在上海开的第二家老洋房餐厅。洋房里的家什都是老古董,有点公馆的派头。底楼客厅就是大堂,每天晚上有老先生在那里弹钢琴,桌椅摆放得很宽松,楼上的包房非常私密,餐具和摆盘都很精致,服务也很周到。
这里做本帮菜。除了上文所提菜肴,张爱玲菜单里还有酒酿饼、糖炒栗子、素鹅、冷切牛舌、糖醋小排、荷叶粉蒸肉、贵妃鸡、虾仁吐司、茄汁鱼球、神仙鸭汤、桂花拉糕、栗子蛋糕等。但是这桌宴席属于限量典藏版,一般是定不到的。不过,万幸的是福1088的常规菜单上包括了 “张爱玲菜单”中的部分菜品,如熏鱼、蜜汁火方(“红玫瑰与白玫瑰”)、郎姆酒葡萄干冰糕。你可以再加点些其他本帮菜凑成一席,人均在350元左右。
奥维斯:“张迷”必到的“后起士林”咖啡馆
“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且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张爱玲
张爱玲住在常德公寓的时候,每天都会被隔壁起士林凌晨烘面的香味所唤醒。起士林原本是天津的品牌。清末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有一个随军德国厨师名叫起士林,德军撤走后他留下来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西餐馆,供应自制的面包、咖啡、糖果以及德式、法式大菜,结果大受欢迎,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西餐走上了天津人的餐桌。如今起士林在天津已经升格为起士林大饭店,这栋四层欧式建筑还被列为天津历史风貌建筑,坐落于市中心小白楼商业区内。
当年张爱玲曾在天津生活过,没想到后来她辗转到上海后,起士林居然也跟了来,而且就开在她家隔壁!张最爱的是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厚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与美国加了防腐剂的软绵绵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按她姑姑的讲法,这面包可以不涂黄油,白吃。
寻踪提示:
起士林上海店的原址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现在已被中欣大厦所取代。有趣的是11年前,一位顾姓上海MM却借此典故在附近的小洋房开了一家奥维斯(Always Café),很快就成了“张迷”必到的“后起士林”咖啡馆,一个美丽的误传被发挥到淋漓尽致。
奥维斯的门牌号是南京西路1528号,一楼外廊的玻璃阳光房经常坐满了老外,里边上下两层都设计成老上海格调,美女月份牌、老式无线电、吊扇灯和大大的铜镜充斥其间。但这里在装饰上并没有刻意强调张爱玲元素,顾MM认为,张爱玲很洋派,见识多,是当时上海的时尚女性代表,所以她的咖啡馆也强调一种无国界料理概念。中午这里提供中西式商务套餐,20元到35元四档价位,花样层出,饮料畅饮;下午是下午茶时间,法国点心师做的巧克力蛋糕、焦糖布丁等等绝对对得起48元两位的价格;入夜,红白朝阳格桌布换成了正红,温馨的桌型也变了罗曼样,爵士乐和蜡烛一旦到位,俨然成了正式的西餐厅。
千彩书坊:一杯咖啡成就一部《倾城之恋》
有兴致时,胡兰成亦随了张爱玲去静安寺街上买小菜,到清冷冷的洋式食品店里看看牛肉鸡蛋之类。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背地里却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淳子
常德公寓成就了张爱玲和胡兰成,张胡二人成就了《倾城之恋》,而成就《倾城之恋》的便是常德公寓底楼的一家咖啡馆。
在常德公寓还叫爱丁顿公寓的时候,张爱玲和姑姑就先后住在501和605室。张每天下午都会到楼下的咖啡馆孵着。这一孵就孵出了一部《金锁记》和一部《倾城之恋》来。
不过此地叫她迷恋的却不只是咖啡香。从阳台上可以瞧见佣人提了篮子去买菜,还可以听见各种叫卖声。卖草炉饼的年轻健壮的声音和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喉咙唱起了对台戏,卖馄饨的则一声不出,只敲梆子,所以她关于“丝袜吊篮馄饨”的浪漫念头也只好作罢。不过这些东西都是解馋用的,上不了台面,招待客人还得用牛酪红茶和咸甜具备的西点。
寻踪提示:
常德公寓去年进行了修整。墙面恢复为奶黄色和枣红色,公寓大门依然紧闭,一张“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字条将“张迷”一概拦住,张望进去也只有一扇绿哈哈的电梯门。
公寓底楼住进了两个新邻居。南面一家叫千彩书坊(colorful),据说去年“十一”还没开张就发生过“张迷”拜访等开门的盛景。书坊室内的位子布置成老上海格调,有怀旧花墙纸和制服笔挺的boy。几排书架上放着收藏、老上海和张爱玲三类书,不定期更换增补,客人可阅可买。其中最受欢迎、经常脱销的是《张爱玲美食地图》、《倾城之恋》和描写张爱玲、苏青与胡兰成的《他们仨》。买书看书的都是普通“张迷”,陈子善之类的知名“张迷”喜欢带人来这里谈事情或者开派对。对他们而言,那些字句早已烂熟于胸,求的也就是个腔调。书坊的室外是庭院雅座,可见石瀑景观。
这里以提供各类咖啡、养生茶为主,价格在20-50元之间。西点不是出自张爱玲菜单,用的是隔壁宏安瑞士大酒店的产品,因为是定制的(比如芝士蛋糕采用双倍芝士等),所以价格要贵一些。
据了解,目前书坊还属于试营运阶段,这里的老板正打算对店装修和菜单进行调整。室内的赝品油画通通要换成当代画家的作品,为墙上张爱玲那张标志性的照片寻觅更好的版本,庭院里增加绿色植物、鱼缸等,菜式上引进意面等西式简餐和红酒,延长营业时间等。
飞达咖啡馆:那念念不忘的乡愁
“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张爱玲
张爱玲寓居重华公寓的时候,在文章里从没提过隔壁的梅陇镇酒家,而是钟情于飞达与凯司令,以至于晚年侨居国外,还念念不忘——“加拿大的香肠卷从手艺上比不上以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油大又辛辣”、“纽约一家丹麦人开的点心店里,拿破仑比不上飞达的好”,尝了当地报纸推荐的起士条后,却还道“还是飞达拿手”……
这家让张爱玲念念不忘的咖啡馆当时就开在平安大戏院隔壁,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匈牙利籍退伍军人所开。” 因上海滩头面人物都喜欢约在这里谈事,所以飞达有着“行政人员咖啡店”之称。
飞达的蛋糕的确做得好,他家的蛋糕师傅凌庆祥后来跳槽出来与朋友合股经营“凯司令”,两家店相去不过百米。跳过隔壁的梅陇镇酒家,飞达与凯司令好比一缕香上的两生花。可惜飞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关门了,而凯司令却作为知名老字号一直留在了繁华的南京西路上。电影《色戒》大红大紫的时候,小说里的王佳芝就是在这里焦虑着抹香水的。但张爱玲对凯司令的环境不甚满意,说那里人气不足,光线暗淡,所以才合适约见。
寻踪提示:
南京西路1129弄就是以前的重华新村,尽管弄堂口新挂的牌子叫“安乐坊”,但弄堂里的宣传栏上依旧是“重华社区”的字样。张爱玲的居所是11号二楼,就在弄口第一排房子的最里面一幢。现在是普通民居,与一家小公司贴隔壁,外观上的派头是一点也没有的。但比起飞达消失的命运,大概还算好些吧。
大大的“K”字悬在凯司令的门面上,底楼一半是蛋糕柜台,另一半则出售进口巧克力和咖啡。最受欢迎的当属栗子蛋糕,大部分都是栗蓉,只有底下薄薄一层是蛋糕,并且还有不同规格适合不同需求。跳过二楼的糖潮,三楼是凯司令的西餐厅。可惜这家餐厅与张爱玲喜欢的精致相差甚远,位子坐起来不是很舒服,菜品也有些粗糙,但价格还是相对便宜的,逛街累了歇歇脚差不多。
老大昌:今非昔比,一声叹息
“离学校不远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各色小面包中有一种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点酥皮,底下镶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比较硬,里面掺了点乳酩,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张爱玲
张爱玲笔下的这家老大昌位于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对面,所谓的“学校”指的是她短暂就读过的圣约翰大学。
这种俄国面包让她到东到西都牵肠挂肚。有回在香港一条僻静小街上发现了一家老大昌,张爱玲几近狂喜,可惜楼上楼下找了一圈,只发现寥寥几只两头尖的面包或者扁圆的俄国黑面包。她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回家发现黑面包硬得像石头,切都切不动,好不容易切开,里面居然有一根棕红色的长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张爱玲文字中有记录的另一家老大昌位于国泰电影院的对面。那时她在霞飞路上的伟达饭店(现已拆除)才住了两个星期,就迷上了老大昌的肉馅煎饼。多年后她在日本的一户土耳其人家吃饭,主人请她吃馅饼,她就说有老大昌的味道,但没有老大昌的好吃。
寻踪提示:
伟达饭店后来变成了襄阳路市场。时光荏苒,现在连襄阳路市场也不复存在了。
淮海路的老大昌呢,虽然现在也没了,但长期人气旺盛,因为张爱玲的肉馅煎饼,因为王安忆的芝士烙面,也因为普通上海MM的掼奶油或者哈斗,甚至连红房子西餐厅的冰糕在当时居然也是他们家加工的。
现在,上海有一家叫 “新老大昌”的西点房连锁店。这是老大昌食品厂与新加坡麦莉食品公司合资经营后新创的品牌。店面分布在浦东齐河路、昌里路以及瞿溪路的海上梦苑菜场里,地段档次是直线下降啊。幸好东西看起来还比较卫生,价格也适中。现在,掼奶油、哈斗和冰糕都还有卖,晚上五点后打八折。
舅舅家的米苋:像捧着一盆的西洋盆栽
“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呼呼的苋菜香。”——张爱玲
张爱玲和母亲住在开纳公寓(今开定公寓,武定西路1375号)的时候,她舅舅就住在对面的明月新村。张妈妈回上海的主要目的是设法让张爱玲去英国读大学,因为张和母亲和舅舅是一对孪生子,感情很好,所以平日里没事他们几乎每天都去舅舅家吃晚饭、聊天,并且带着一碗米苋。这个舅舅对张爱玲也是另眼相看,肯花时间给她讲家族故事,因此张笔下的米苋是有点兴高采烈味道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敏感的女人最最吃不得的是姑姑的包子。有一次,姑姑忽然很高兴,因为张爱玲想吃包子,便用芝麻酱做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张爱玲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东西吃下去也不知有什么味道,只还是笑着说好吃,好吃。
寻踪提示:
开纳公寓清水墙面,5层楼高,楼内套房四周镶有柳安木护壁,蜡地钢窗、壁炉、水汀、大小卫生设备俱全,在当时属于比较高档的。开纳公寓现在的住户基本都比较警觉,对张爱玲是一点不知的。
明月新村是新里住宅,据说当年是以业主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三层高的房子,一共16幢。每幢房子都有一个玲珑的天井。黄昏时,这里有时也会飘出人家炒米苋的香味,算是一种最为朴实的纪念罢。
国际饭店大堂咖啡吧:与胡兰成的最后一次幽会
为了避嫌,他们彼此装作没有看见。——某知情人
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居住地点是位于黄河路65号的卡尔登公寓。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张爱玲的母亲最后一次回国,就下榻于国际饭店。更加叫人魂萦梦牵的是,饭店大堂的咖啡吧是她和胡兰成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据某位知情人讲述,上世纪50年代初,逃亡中的胡兰成曾经偷偷地回过上海,秘密与张爱玲会面,不料却在国际饭店撞见一个熟人。结果为了避嫌,他们彼此装作没有看见。
寻踪提示:
当时的卡尔登公寓地板全部采用细柳安木,并配备高级卫生设备。公寓里处处是铜制的把手、锁、徽记,并设有四架楼梯,供不同层次的人员进出。现在这里叫长江公寓,住户大多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搬进来的。
现在的国际饭店大堂咖啡吧有点萧条了,咖啡38元一杯,蛋糕之类的点心少得可怜,连个下午茶套餐也没有。如果张胡二人约在今日,怕是不会再遇见什么熟人了吧。在偌大的空间里,对坐着,任凭咖啡香在两人之间绕来绕去,不是酸,就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