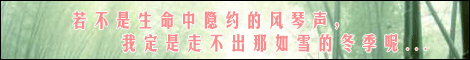天下奇闻:大巴山野人闯进鲁院! 
(第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中鲁十一学员和鲁院副院长白描在一起)
毛竹活到这么大,一共才打过十多次乒乓球,可是在鲁院毛竹已经打过二十多次乒乓球了。这一定鲁院作家的大气场GD的。这是毛竹在鲁院打乒乓球时的芳影。羊角岩摄)作者简介:毛竹,女,笔名竹子、东方竹子、巴山女子、东方散人,佚人等。毛竹出生于大巴山区已经破败的毛和兴老商号堂屋中用竹篱笆围出的倾斜半屋内。按当地风俗,大巴山地下三米埋着毛竹的胎盘。在大巴山,老商号的堂屋是供神祭祖停灵放棺的地方。三百年历史中有多少毛家大事在这堂屋里决策,有多少位毛家先人从这堂屋出殡。堂屋是不能住人的,怎么会有女娃子生在老商号的堂屋?可是千真万确,毛竹确是一个生在堂屋的女娃子。毛竹的出世带出数个难解之谜。毛竹后随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爸爸在青藏高原“支边”二十多年。毛竹毕业于中国“最破烂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数学系。民院的老师有全国的支边精英,有塔尔寺的活佛,有清真寺的阿訇,草原上的王爷.毛竹不仅是青华大学的吴中英、复旦大学的余德元、北师大的朱聘瑜特别欣赏的高才生。毛竹上大学时班禅曾来校视查给毛竹摸顶。班禅经师嘉雅活佛特邀毛竹参加。塔尔寺寺主阿嘉活佛给毛竹摸顶后不久逃国外找达赖活佛。毛竹的大学校友更是以青海六大主体民族为主的各类“原始部落人”。毛竹现为中国石油报社记者。被文人子们亲切地称作“大巴山主峰神农架神秘美丽的女野人”,“青藏高原戴骷髅项链的雪山女神”。毛竹出书多部:《迷失在西部》、《透明的性感》、《透明的女性》、《透明的激情》、《透明的分娩》、《生命的隐衷》等。几百万字散文、杂文等散见各报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为她的书首开中国出版史上贴防伪商标先河。中国社会出版社为她首开中国出版史上长篇探索女性系列丛书先河。毛竹曾十几次在全国音乐文学大奖赛中获奖。毛竹今生今世与埋入她胎盘的大巴山与养育她的青藏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下奇闻:“大巴山野人”闯进鲁院!
毛 竹
3月9日下午,我自己开车,由于技术不行,歪歪扭扭横冲直闯地来到鲁院。
GPS指挥的路线很奇怪,让我下了二环走了数段“小路”,然后来到一条渠边“瘦”路,“瘦路”的两头还有两个粗筒状路卡,小心翼翼地过了第二个路卡,然后右转,这才绕到鲁院大门口。
鲁院的大门口有警卫,我乖乖地拿出鲁院第十一届高研班的入学通知书才得以进入鲁院大门。
回望,那个在作家眼里神圣的鲁院大门!我这才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
一进鲁院主楼的玻璃大门,我就看到大厅中一长排桌子后面几位老师“排排坐”只是不是“吃果果”,而是恭候着我们学员的光临呢。
我填了表,交了1千元钱,就算是正式的鲁院学员了。老师告诉我:这1000元中600元是伙食费,350元是电话押金,50元是钥匙押金。
我知道,这一次,学员的学费、住宿费、实践活动费等全部由中国作协提供,学员基本不用花钱,除了伙食费和电话费。因为我们这届学员被称做国家重点培养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呢。
四年前,我工作的中国石油报社从涿州来到了北京,可是却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来京的:就连我们的办公室都是租的:—座五十年代修的老办公楼的五楼。那五楼的几个房间发出奇怪的味道,怎么也消不除,据说是因为这五楼是在原楼的房顶上加盖出的。有味的原因据说是加盖五楼时楼顶没打扫干净,或许是有死老鼠什么的,故而有这怎么除也除不去的怪味儿。还好,我们的大办公室味道不行!我这个喜欢郊区、喜欢农村、喜欢大山、喜欢森林、喜欢溪水、喜欢动物,喜欢飞鸟的原始人也不得不随着大潮来京闯荡。我从一个小城里的贵族,一个乡下的皇族,一下子坠落到大城市的最底层,成为京城滚滚红尘中最小的一个蚂蚁。我们成了北京啥也没有的彻底的流浪者。
由于中国石油最近已经跃居世界四百强企业第二位,中国人没有人能相信我们这些被迫进城的酸文人的尴尬处境。
可是由于中国石油A股下跌套牢全中国人民,由于油价下跌,我仍时时湮没于在全中国人民骂中国石油的滚滚唾沫汇成的浪潮中,风雨飘摇。
我们中国石油销售零售时一吨贴一千元没有中国人民知道,外国飞机在中国加一箱油中国石油亏十几万没有中国人民知道,可是国际油价才降几天,中国石油的油价比国际油价高全国人民都知道。全国人民都骂中国石油大赚垄断黑心钱。最近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上涨,没有知道油价是国资委调控,决策是按国际股份公司贯例行事。有一次我们一位副总,在记者采访时实话实说:“我代表国家垄断你!”一时间掀起轩然大波。此副总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我们这些小蚂蚁也跟着一次一次挨骂。我们中国石油的董事长都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一连换了二位:因为开县井喷,因为吉化爆炸。因中国石油A股套牢全国股民,第三任董事长又辞股份公司总裁职备。何况我们这些小蚂蚁?风雨中我仿佛一下子丢失了脚下的泥土,一下子被抽去了身后的家园。
这几年,我的写作完全不在状态。网上呈现的是我过去作品的好时光。维持名气的还是一个作家过去作品的惯性。只是我都感觉奇怪,这个惯性居然会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多地越居各种排行榜。在搜狐中搜索“女作家”“美女作家”等毛竹居然都排名全中国前十位。毛竹居然被“中国作家网放在主页”。毛竹居然“作家在线网”冲剌在文学网站前沿的三位女作家之一。真没有想到我那些困惑迷茫时的“排泄物”,我那些绝望无助时的“大瘤子”,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的读者拾起来反复把玩。
就是出版社的人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追我要书稿,就是著名出版家安波舜、岳建一、向飞亲自上门约稿,就是我也经常和我的编辑一起探讨我将交的书稿,就是我也偶尔给出版社的某位社长说着我将交的书稿。可是,我也只是说说,连交稿的这最后一步我也没有去做。虽然我的好几部作品的创作只差最后一步。
天下还有这样的怪事情,我说完了,编辑在那里苦等,出版家在那里关注,社长们在那里期待,读者埋伏在全国的山山水水全心身期待着东方竹子作品问世,而我自己反而忘却了,只顾行色匆匆。
因为进京,我不得不离开感情颇深的青海作协和河北作协,可是北京作协的门在哪里?中国作协在哪里?
这几年的我,只在网上写一些小的文章,就仿佛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汇入滚滚红尘感觉生命的潮起潮落。就如一只小小的蚂蚁驾着一叶苇草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在狂风浪潮中冲浪。只能感受生活的潮起潮落,其它根本顾不上。
有时,终于夜深人静了,我却不能静在下,大海的潮声仍在我的耳畔喧哗,潮涨潮跌,我无法隐退。大海的浪头不时扑向我,我抱住头仍弄得一身都是咸水。我只能身不由己地打开电脑,装成一个旁观者,不看我这只小小蚂蚁怎样驾着一叶苇草在网上冲浪,不去感觉它们不时地冲上浪尖,不时占据潮头。
当然,也有一种驾一叶小舟冲浪在大海中才能感受到的新鲜和剌激。
不由想起这样的诗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
这几年,我唯一能做的事件是写了大量身边人物的散文,什么写《废都》的贾平凹,什么《狼图腾》的策划安波舜,什么《藏獒》的作者杨志军,什么《血色黄昏》的运作人岳建一,什么《第二次握手》《男一半是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的运作人顾志城,什么央视五届春晚总导演郎昆,什么凤凰卫视刘长乐、窦文涛、吴小莉,什么中国社会出版社贾斌,什么动漫小破孩子之父拾荒田易新,什么“马玉涛的第一夫”雪藏在青藏高原冰洞中的青海音协主席靳梧桐“,什么跳楼自杀的著名诗人昌耀和竹子低语,什么著名散文家尧山壁佚事,什么得癌症的肖复华,什么“山西怪石,写《寻找巴金的黛莉》的赵喻”,什么阳光卫视杨澜,什么电影名星刘晓庆,什么《牵手》导演杨阳,什么京城四大名编之一崔道怡,什么文学名人陈元魁、林惜纯、白渔、朱奇、肖杨、郭秋良、杨兆祥、樊廉欣、田耒、石英、邵华泽、卞卡、李若冰、雷达、李炳银、刘茵、张守仁、曹杰、梅洁、梅卓、杨凌波、王玉民等,我居然写了几百个名人。我写了这些名人却并不推广,只是放在我谢绝推广的写稿网中的孤芳自赏。偶尔拿出几篇放在我被我冷落多时博客上,不久,我一时即兴的小文章居然能冲浪到风口浪尖,有的甚至成了定位某位名人的重要文章,被人反复阅读。
“可能若干年后,你感觉,你已经不是你,而毛竹笔下的你才是你!”
我没有想到我从来不知道我还有如此“天才”呢!
我甚至当起了评论家:评导演张艺谋“周杰伦的歌曲《菊花台》是《满城皆是黄金甲》的断尾巴”。评导演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无论发生什么,太阳照常升起”,评导演陈凯歌的《梅兰芳》“拍了半部好片子”,评电视大导杨阳的《记忆的证明》:“中国人也当反思”…我居然还可冒充评论家呢!
我甚至当起了杂文家,什么《国美妄想断头生存》,什么《“杀富”还是“救富”,法制社会我们当如何选择?》什么《建议国家建立美丽浪漫的爱滋新城》《建议富士康管理人员先回家养只宠物猫》……我居然还可冒充杂文家呢!
仿佛是我感觉自己这个小蚂蚁太太渺小了,想多粘一些蚂蚁,和我抱成团滚动。这是面对宙宇深渊、地球裂缝的恐怖感在征服了我,让我的无助百倍千倍扩大,感觉只有抱成团才能给自己壮行色,只有结成队才能给自己壮胆量?我不知道!我以前只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只关心我自己,我独立创作,我孤家寡人,我孤芳自赏,我与世隔绝,我面壁十年,我自闭症患者,我和社会严重脱节,我似乎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泥潭中解脱出来,自救出来。
除了报社必做的工作,我每天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在网上看房子。东看看西看看。而业余时间能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汇入滚滚红尘中的某股人流四处看房子,东看看西看看。虽然知道了我的生命注定要四处飘泊,可是还是想把飘泊的生涯固定下来。而我正是通过看房子不断了解着这个北京这个陌生的大城市。
我似乎无法静下来想一想,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地身不由已?我为什么总是被大浪扑来扑去。我为什么总仿佛被神秘的大力挟持。内心里伤痕累累。可是我却无法停下来抚摸它们,我只顾冲浪,我根本顾不上其它。
没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种空前绝后的恐怖状态中我失去了爸爸,永远地失去了爸爸。我这个以爸爸为敌的叛逆女儿,痛定思痛,第一次想到了一个词,那就是“回归”。
而这一次的回归,又一次带着博大的气场,就如当年我一个柔弱女儿身不由己离家出走,把命提在手上沿汉水沿毛家祖宗的足迹万里寻根一样。
而这种回归,有代表性地表现在两件事:一件是我终于认真地准备参评高职。我第一次认真地参加了各种高职考试--以前我也参加,可是却根本心不在焉,参加三次英语考试却从不复习――我上大学学的是藏语,石油专业英语我不懂,我去考只是因为我是无奈的,是爸爸要求我这样做的,是爸爸逼迫我这样做的,我是身不由已的。
由于我第一次认真对待我的评高职,好消息也阵阵传来。我来鲁院之时,我的高职在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评审时,以最高分通过,现在已经进入在中国石油报公示阶段。
我拗着劲儿不交书稿不再出书,其中一个因素似乎也是和爸爸拗着劲儿:我耿耿于怀的是:爸爸在我写作黄金时期却要求我加入传统的评职晋升,提醒我不要放弃太多,于是天生叛逆的我就什么都放弃了,我感觉自己很悲壮。是我和爸的传统思想拗劲还是我和爸爸的爱拗劲?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气场和爸爸气场天生相悖,我们实在是像是天敌一对。
在我的心里爸爸是世界上精神力量最强大的。我要和这股精神力量拗着。
爸爸真的逝世,我怎么才能摆脱我是杀手我是罪人的内疚心态?
我这个天生以爸爸为敌的人,在听不到爸爸的话时才第一次听了爸爸的话。
我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争取上鲁院。我知道这不仅是我生命的需要,还有我爸爸灵魂的需要。很多年前,当我还在涿州上班的时候,鲁院当时的副院长雷抒雁就特别看好我的写作,就多次请我来上鲁院。
我嘴里说我没有一整块的时间。实际上是婉多次言拒绝。我这个山里人,虽知天高地厚、师傅重要、培训重要,但却天生逆反,不愿加入传统作家的行列。我这个叛逆的女儿,我这个时代的黑马,我这个离家出走的母鹿,我这个孤独游荡的孤鹰,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山鹤,我这个大巴山主峰的野人,我这个青藏高原的原始人,我不仅和爸爸叛逆,和一切传统的东西叛逆,当然也和全中国的作家叛逆,和正规的作家教育叛逆,和正规的全国评奖叛逆—我在石油文协组织评奖时我就放弃过只要交作品就能得的大奖。
那些年我的作品销畅大江南北时,得到中国一流名编:张守仁、崔道怡、石英、林菲、卞卡、岳建一、张雅南、尧山壁、顾志城、贾斌、安波舜、岳建一、雷抒雁等的关注,被中国一流的评论家雷达、古耜等看好。可是我居然从不愿参加过“鲁奖”“茅奖”的评比。自认为是“铁打的作品,流水的评奖”我自以为写作只需深情地面向读者就可以了。
我知道鲁迅曾是上一个时代的逆儿,可是现在鲁迅成了传统的代名词。我更认为我只有不上鲁院,才能做这个时代的叛逆儿。我自认为我是大自然之女,我是大山之魂,我是溪水之魄,我是森林之精,我是野生动物之灵。
我欣赏杨丽萍拒绝集中练功保住那种自然天性;我喜欢唱《一个妈妈的女》那个梳无数小辫子的青海藏族歌手德乾旺姆拒绝进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以保住天籁般歌声,我赞同女儿国的杨二娜姆带着山水特性不被凡尘同化,我惊喜不识谱的阿宝能吼出这个时代最后几声属于原始生命的野啸。
我喜欢写《海狼》的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我希望像他一样一般一次一次狐独出海,哪怕我最后如海明威一般收获的只是一巨大的白森森的鱼骨。
我一次一次婉拒雷副院长的要求,是因为我要做我自己,与众不同的自己。我要向立潮头,站在反传统的风口浪尖迎风破浪,我要一个人对峙强大的中国作家团队。我要做孤家寡人。我要寻找一个支点,试试能不能撬动几千中国作家会员组成庞大的阵营。
对!我要在骨子里和全中国的作家对着干。
对!我要在骨子里向整个中国作协宣战!
对!我要在骨子里和整个中国文联的阵营为“敌”,我要向他们发起总攻。
小小我要以一个人的柔弱之力和传统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在市场上对峙。小小的我要以一个人微薄之力和从鲁院----中国作家的黄埔军校出来的作家团队在写作质量上对峙。
是的,我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写作。我要警惕全中国的作家同化我。我要避免和他们清一色。
我怎么能上鲁院呢?
我要上了鲁院我不就和其它作家一样了吗?我要上了鲁院我还是大巴山野人吗?我要是上了鲁院我还是青藏高原原始人吗?我要是上了鲁院我还是酋长部落人吗?就是因为我没上鲁院在写作上我才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呢!
我宁肯做一个小螳螂悲壮地以细细的手臂以小小的生命挡滚滚时代大车,那怕我被碾得血肉横飞,那怕我被碾得灰飞烟灭。因为,这种对峙带给我无限的激情和无限的快感和无边的剌激呢。我需要这个!那真的是一种向立潮头,乘风破浪的感受呢!
可不是?我孤独无助!我独立无援!我势单力薄!我孤家寡人!可是我的精神上却高度亢奋,高度富有!高度充盈!
我快乐呀!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作家呀!因为我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对手,有那么多的"敌人"呀。
我快乐呀!因为我没有组织,因为我不要帮助,因为我不要后台!因为我只代表我自己!
因为我就是我,所以我的感受如此独特!我的见解如此特立!我观点如此新鲜!我的文笔如此流畅!我的感情如此准确!我的灵感如此泉涌!就是因为我没有上鲁院呀!
我有时还感谢神灵,让我上大学前从没有受过几天正规教育。我有时感谢魔鬼,让我上大学学的是数学而不是文学。我有时感谢佛祖,让我上的是中国“最破烂大学”,那里芸集着中国精英,青藏活佛,青藏阿訇,草原王爷,草原游牧人,天葬台天葬师,让我可接触青海高原形形色色的“野人”“原始人”“部落酋长”。在文学创作上,我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我没有任何的思想禁锢。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才思敏捷光芒四射,我如孙猴儿可上宇宙揽仙,可下地狱请魔。
我有时感谢妈妈把我生在大巴山竹篱笆中。我有时感谢谢我有一个会爬树摘柿子会唱山歌的妈妈。我有时感谢爸妈让我在河湟流域山野中玩大,我有时感谢我长在中国最荒蛮的青藏高原。我有时感谢爸爸对我粗放型野放式的教育。我有时感谢我的十年启蒙教育几乎一片空白。我有时感谢我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数学被称作世界上最美的诗!
我是大巴山野人,我是青藏高原原始人,我是石油酋长部落人。我要的就是这一点呀!
我有独力的思辩能力,我有独特的创新能力,我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就是因为这个呀!
一个回合下来,小小的我,一个从最中国最落后、最原始、最封闭、最偏远地方来闯京城的小小女作家的书,就小获胜利,初见分晓:我的书"透明系列"销畅销天南地北,上可进文学圣殿新华书店,下可进地摊拉圾站,在中国引起一次一次响动。别的人出书要么自费要么只印几千,而我的书四十万字的大本每次开印都上万,且多次再版,且创多年入排行榜奇迹。每次都让出版社大获全胜满意而归。
这使得我越发自以为势,越发离鲁院渐行渐远,离正规的作家教育渐行渐远。
这促使我更拗地更犟地去钻“牛角尖”。更加孤注一掷地向立潮头。
而我的记者工作对我的挑战更大。更何况我不是专业作家,我在活水中,我还有那么多的正事要做,那么多的企业家要采访,那么多的名家要探秘,哪有时间不务正业。写作也要等我这个野人、我这个原始人、我这个酋长部落人高兴时再写。这使我这个说是知道天高地厚,其实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毛人、小野人、小酋长部落人离鲁院更加渐行渐远。
直到爸爸逝世,昏天黑地之后,我这个和爸爸叛逆离家出走多年的女儿才终于想到了回归?
我终于停下来,回望和我失之交臂的鲁院。我看到被我遗留在岁月之河那一边的鲁院,像在水一方的“佳人”,在烟雾迷漫中隐现。而那条岁月之河中跳动出没闪动闪烁的,却仿佛是我这些年经历的酸甜苦辣。

前年--处理完爸爸的后事回京,我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带车来了一趟鲁迅文学院。那一次我拜见了王彬副院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表达我想上鲁院的梦想。这是我在感觉不到爸爸的愿望时第一次按爸爸的愿望行事吗?我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受中央表彰的高才生,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人大度过的。他老人家一定是希望我既然要从事写作首先就是能进鲁院上学?他老人家一定是希望我既然要从事写作首先要向中国作协组织靠拢吗?爸爸一直一直担忧的就是我创作上一直保持的大巴山野人、青藏高原原始人、旷野上精神游牧人、灵魂上吉卜赛部落人状态吗?
我来上鲁院,这同样是我在已经感觉不到作协对我的关爱之时第一次按雷抒雁副院长的愿望行事吗?中国作协的邀请函我接到多次,可是今年叛逆的我才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团拜活动,
但是,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这些年,我已经走得太远,根本就要游离出中国作协的视野和管辖。
我是在宣布我这个叛逆的女儿,我这匹社会的黑马,想回归一次正统?看看正规的作家院校是怎么教育作家的?或许,多年以后,我还会突围出去,但是我这次屈服,绝对是有深刻内心原因的,绝对是有深刻灵魂因素的。
而我没有想到,我想上鲁院的愿望一经从心里冒出来,就如搬开了一个清泉上的石头,那泉水,汩汩涌流出,一下子就漫天漫地汇成茫茫大海;那海潮,波涛汹涌,一瞬间便轰轰隆隆带出山呼海啸。似乎我不马上去,我就会被淹死掉。而我更没有想到这愿意一经我的口表态出来,我便显得那般不屈不挠,那般百折不弯。我跑去见中国石油文协的北原,表达了我想上鲁院的愿望。中国石油文协一直是想重点培养我的,只是捉不住我。于是,去年的通知一下,就把指指标特意地留给了我,却只是一个青年作家班。怎么办呢?报社假已经批下来了,想来想去不甘心,还是想上,决定冒进。总感觉如果我不上就再也上不上鲁院了。就好像我不上鲁院我就从此再也当不成作家了一般。
我“明知故犯”,拿着鲁院的通知书上蹿下跳,我找报社人事张文业、中国石油报社副社长邱宝林、社长白泽生一一签字批示,我找人事处杨文清盖章,我送交文协请北原盖章,总算是批下来了,我又关照文协安琪邮寄表格。中国石油文协把我的表报到鲁院了,我的心却揪在一起了,我担心批不下来,因为我已经过龄,其实我也不愿意和“八零后”在一起学习,可是为了上鲁院,我没有办法,只能背水一战。我甚至和石油文联秘书长路小路打了招呼。我甚至找了原中国石油地火主编田耒找到林林菲,找到了原鲁院副院长雷抒雁的手机。
还好,中国作协批下来了,鲁院也通过了。
正当我高兴之时,没想到我高兴的太早了。
白描院长有一天给我打来电话:“毛竹,我和你商量一下,把你和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的、陈忠实作家推荐的、八零后小姑娘换一下,你明年再上。我给你保证!”白描院长亲自给我商量,又保证我明年定上,我只好答应了下来。可不是?如果这一期多是八零后,我和她们在一起也实在尴尬。我虽然答应的白描院长,但感觉却很绝望。过一年,报社还能给我四个月的假吗?我还需要找那么多领导签字盖章吗?我还能上上鲁院吗?
可是既然我想上,我就一定要争取。我仿佛在做人生第一件实事。我仿佛从来没有这么拗过,而且一拗就要拗到底的架式。
今年新年一过,我就瞄上了中国石油文协的北原,吩咐他鲁院通知一来了就告我。北原担心再被人顶规孤注一掷地只报了我一个人。我瞄上了鲁院的白院长,跟踪鲁院下通知的进程。我甚至准备万一不顺就给铁凝、金炳华、陈建华、金坚范等领导打电话。我知道,中国石油如果比出书量畅销度我可能排第一,但是中国石油人才济济我仍有可能被涮下。通知终于下来了,我又是一番上蹿下跳,在中国石油报白泽生、邱宝林、张文业、杨文清,北原、安琪的齐力热心帮助下,在白描副院长、王彬副院长、雷抒雁大诗人的特别关照下,在严迎春等老师的努力下,我终于如愿。这会儿,我这个相信天缘的人,喜欢顺其自然煌人,第一次想起著名作家、萧乾夫人文洁若给我题的字:“事在人为!”
我知道,竹子上鲁院和别的作家上鲁院一定是不同的,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竹子是野人,竹子是原始人,竹子是酋长部落人。野人上学本就是一件稀奇事情。原始人上正规学校那更是一件稀奇事情。酋长部落人上作家的黄埔军校那更是天地间一件稀奇事情。可能所有熟悉竹子,了解竹子叛逆天性的人都会感觉十分奇怪。可能所有熟悉竹子骨子里野性喜欢竹子骨子里野性的人都会长长叹息。这也叫否定之否定?
是我爸爸的幽灵在冥冥中指引我来上鲁院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正是爸爸去逝后,我这个叛逆的女儿,终于开始回归,第一次考虑在写作上暂时不做一个大巴山野人,不做一个青藏原始人,不做一个酋长部落人,加入作家的黄埔军校,回归一次传统。
当然细想,我想上鲁院的愿望可能还我进京后的状态有关。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女子,一个喜欢田原大山溪水的女子,更哪堪离开真元原之气,经历灵魂精神肉体三重的漂泊?而来京后我的忽上忽下乱七八糟的工作状态,我的四处飘泊八方流浪的野人生活状态。加之我这些年延续的一种寻魂找魄虎追狼赶的疯狂岁月,我的堆积的张慌失措恐怖凄惶心理状态。
走进鲁院,我的心里暖融融的,那是一种终于回归一次正统,终于回归一次老家的感觉。那种感觉就似我这个叛逆的女儿当年离家出走多年后,终于回一次青藏高原的感觉。那种感觉就似我这个叛逆的女儿跟爸爸离故土出走二十多年后,终于第一次回大巴山区的感觉。我回望玻璃后鲁院的松树竹子亭子,我禁不住从心里微笑起来。
这些“排排坐”的老师们也不给我们互相介绍,只介绍其中一位:“这位就是严迎春老师”。严老师负责给我们发通知,老师们都知道除了副院长白描,王彬,成曾樾、后勤处王俊峰我们都只和严迎春“熟”。我一回头一看:“哇!严老师,这么年轻呀!”在报名推荐填表过程中,严迎春老师的敬业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报完名,我拿到了单人宿舍的钥匙上楼。一进门,我看见房间很小,每人一个标间,电脑、电视配套。里面有电脑,有电视,有电话,有台灯,有小衣柜,虽然比我上大学时条件好多了,比我这些年采访走四方时住的星级宾馆差远了。不过,没地毯,很可爱;房里阳光充足,很温馨。稍有点可惜是洗手间有点味儿。我在房里转来转去,调整思绪,以期更快适应我的新的“大学生活”。我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把东西归整好,拿着暖瓶去楼道打开水。打完饭一边打电脑几次看表,平时自由散漫惯了,怕错过吃饭时间。五点半了,我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我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躺下呼呼地睡到大天亮。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像一个真正的学生一般。
第二天上午9点,我来到五楼大教室,我发现会场上挂着“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横幅。我找到写着我的名牌的位置坐下,我这才发现我的名牌上除了写着毛竹还写着我的笔名竹子呢。我环顾四围,发现我的边上有粟光华(笔名苦金),澜涛(笔名天下)徐小燕(笔名拾柴)等,我由衷地笑了,多可爱的笔名呀!
后来,我初步了解到我同学中,有去年“鲁奖”获得者山西女作家葛水平,有茅盾文学候选作品《水乳大地》的云南作家范稳,有创网上点击三千万的《元红》杨州作家顾坚,有自称“搞垮过三个企业”的珠海诗人卢卫平,有来自四川地震灾区棉阳市的女作家冯小涓,有电视剧《金粉世家》《红粉世家》的编剧河北西门,有《双枪老太婆》的导演重庆的作家张渝,有天津的实力派作家狄青,有济南军区的部队师级诗人康桥,有山东获冰心儿童图书奖的女作家周习,有北京二炮的青年作家陈涌,有新疆建设兵团的诗人秦安江和伊犁晚报的社长王亚楠,有湖北底层新秀土家族作家羊角岩,有四川土家族作家苦金,的陕西黄土塬作家梦野、有西安名画家吴文莉,有网上新浪原创文学大赛的获奖者北京女作家金子,有天方地圆的中国石化文协的副主席周篷华,有气正腔圆的甘肃文学院院长张存学,有甘肃武威的“思想者”补丁,有中产阶级代表作家上海的女作家孙未,有八零后作家丁天、洪玲、欧逸舟,有歌星经纪人另类作家姜银,有三韩:宁夏韩,海南韩,吉林韩。有卷发高额头的青海的作家原上草,有西藏来会跳舞的作家敖超,有内蒙来会唱《红雁》大学教授作家海日寒,有内蒙赤峰来的能写书法的作家李学江,能跳蒙古舞能主持晚会的作家麦砂,有河南的作家幽默的陈麦琪,有江西思想深邃的作家陈然,黑龙江作家有长得像极雪村的高万红、有能在《知音》杂志一年挣几十万稿费的作家澜涛,有朝鲜族延边歌舞团团长朴长吉,有广东佛山“保彪级”作家吴彪华,有会唱山歌的贵州作家彭彭,有一唱通俗歌就全心身投入摇晃的大连作家陈昌平,有天津铁路会说“天津单口”的作家李小重,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法兰西小姑娘”深蓝,有喜乡村美丽土布裙子的中职推荐的女作家谢凌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来的文静女作家徐雪萍,有“高个相靓声粗”河南的女科技局长作家王相勤等等。
更独特的是:我们这些学员有“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年龄跨度达近三十岁。
只是我们这些作家,老师一个劲说:全国知名作家,可是,来之前我没听说过几位,包括我,也不被他们所知。所谓的“全国知名作家”,就连那些得鲁奖的,也成了文学圈里的事情。而那些在网上红的,比如顾坚,比如金子,比如姜银,在文学圈里却又没有地位。
这样想我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
我去参加在鲁院五楼会议室的开学典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