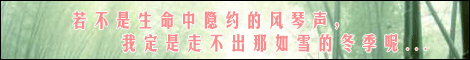野人到鲁院报名第一天
3月9日下午,我自己开车,由于技术不行,歪歪扭扭地来到鲁院。
GPS指挥的路线很奇怪,让我下了二环走了数段“小路”,然后来到一条渠边“瘦”路,“瘦路”的两头还有两个粗瓶状路卡,小心翼翼地过了第二个路卡,然后右转,这才绕到鲁院大门口。
鲁院的大门口有警卫,我乖乖地拿出鲁院第十一届高研班的入学通知书才得以进入鲁院大门。回望,那个在作家眼里神圣的鲁院大门!我歪歪扭扭地把车停在院里--后才知那是个网球场并不是停车场,这才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
一进鲁院主楼的玻璃大门,我就看到大厅中一长排桌子后面几位老师“排排坐”只是不是“吃果果”,而是恭候着我们学员的光临呢。我填了表,交了1千元钱,就算是正式的鲁院学员了。这1000元中600元是伙食费,350元是电话押金,50元是钥匙押金。我知道,这一次,除了伙食费电话费,其它费用如学费住宿费等都是鲁院文学院出的。因为我们这届学员被称做国家重点培养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呢。
四年前,我工作的中国石油报社从涿州来到了北京,可是却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来京的:就连我们的办公室都是租的:—座五十年代修的老办公楼的五楼。那五楼的几个房间发出奇怪的味道,怎么也消不除,据说是因为这五楼是在原楼的房顶上加盖出的。有味的原因是加盖五楼时楼顶没打扫干净,或许是有死老鼠什么的,故而有这怎么除也除不去的怪味儿。还好,我们的大办公室味道不行!
我这个喜欢郊区、喜欢农村、喜欢大山、喜欢森林、喜欢动物,喜欢飞鸟的原始人也不得不随着大潮来京闯荡。我从一个小城里的贵族,一个乡下的皇族,一下子坠落到大城市的最底层,成为京城滚滚红尘中最小的一个蚂蚁。我们成了北京啥也没有的彻底的流浪者。可是由于股市油价,我仍时时湮没于在全中国人民骂中国石油的滚滚唾沫汇成的浪潮中。我们中国石油销售零售时一吨贴一千元没有中国人民知道,外国飞机在中国加一箱油中国石油亏十几万没有中国人民知道,可是国际油价才价几天,中国石油的油价比国际油价高全国人民都知道。全国人民都骂中国石油大赚垄断黑心钱,我们这些小蚂蚁也跟着挨骂。
我仿佛一下子丢失了脚下的泥土,一下子被抽去了身后的家园。
这几年,我的写作完全不在状态。网上呈现的是我过去作品的好时光。维持名气的还是一个作家过去作品的惯性。就是出版社的人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追我要书稿,就是我也经常和我的编辑一起探讨我将交的书稿,就是我也偶尔给出版社的社长说着我将交的书稿,可是,我也只是说说,连交稿的这最后一步我也没有去做,虽然我的好几部作品的创作只差最后一步。天下还有这样的怪事情,我说完了,编辑在那里苦等,社长在那里期待,而我自己反而忘却了,只顾行色匆匆。
这几年的我,只在网上写一些小的文章,就仿佛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汇入滚滚红尘感觉生命的潮起潮落。就如一只小小的蚂蚁驾着一叶苇草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在时代浪潮中冲浪。只能顾生命只能顾活命根本顾不上其它。有时,终于夜深人静了,我却不能静在下,大海的潮声仍在我的耳畔喧哗,潮涨潮跌,我无法隐退;大浪的浪头不时扑向我,我抱住头仍弄得一身都是水。我只能身不由已地打开电脑,装成一个旁观者看我这只小小蚂蚁怎样驾着一叶苇草在网上冲浪,并感觉它们不时地冲上浪尖,不时占据潮头,那种驾一叶小帆冲浪在大海中才能感受到的剌激。
这几年,我写了大量写身边人物的散文,什么写《废都》的贾平凹,什么《狼图腾》策划安波舜,什么《藏獒》作者杨志军,什么《血色黄昏》运作人岳建一,什么《第二次握手》运作人顾志城,什么中央电视台五届春晚总导郎昆,什么凤凰卫视窦文涛,什么凤凰电视台长刘长乐,什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顾志城,什么中国社会出版社贾斌,什么电影导演姜文,什么电影导演陈凯歌,什么电影明星刘晓庆……什么青海音协主席靳梧桐,什么著名诗人昌耀…我居然写了上几百个名人和上几百个普通人。仿佛是我感觉自己这个小蚂蚁太太渺小了,想多粘一些蚂蚁,和我抱成团滚动。这是面对宙宇深处地球静外的恐怖感觉彻底的无助,才需要抱团给自己壮行色才需要结成队给自己壮胆量?我不知道!
我以前只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只关心我自己,我独立创作,我孤家寡人,我与世隔绝,我面壁十年,我自闭症患者,我和社会严重脱节,我似乎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泥潭中解脱出来。
除了报社必做的工作,我每天的业余爱好就是在网上看房子。东看看西看看。而业余时间能做的事情,就是汇入滚滚红尘中的某股人流四处看房子,东看看西看看,想把飘泊的生涯固定下来。而我正是通过看房子不断了解着这个北京这个陌生的大城市。我静下来想想,我是不是想把飘泊的生涯固定下来才这样身不由已地?
没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种空前绝后的恐怖状态中我失去了爸爸,永远地失去了爸爸。
我这个叛逆的女儿,我这匹众叛亲离的黑马,在快被击倒时怎么站起来的,我忘了,其它的我不知道,我只是第一次想到了回归。
而这种回归,有代表性的表现在于这两件事:
一件是我终于认真准备参评高职。我第一次认真地参加了各种职称考试--以前我也参加,可是却根本心不在焉,参加英语考试从不复习――我上大学学的是藏语,石油专业英语我不懂,我去考只是因为我是无奈的,是爸爸要求我这样做的,是爸爸逼我这样做的,我是身不由已的。我拗着劲儿不交书稿不再出书,也不帮助爸爸出书--爸爸是属龙的,事业的成功关系到他的生命,而我却拗着不帮,捂死了这条龙。这个时代的一代精英让留给我用,可是我却不用,并亲手在沼泽中捂死了他,并狠心在泥潭中溺死了他。是我和爸的传统拗劲还是我和爸爸的爱拗劲?我不知道,反正我天气就和爸爸像是天敌一对。而爸爸真的逝世,我却怎么才能摆脱我是杀手我是罪人的内疚心态?
我这个天生以爸爸为敌的人,在听不到爸爸的话时才第一次听了爸爸的话。我第一次认真对待我的职称。第一次带着对爸爸的内疚去做这件我自己的事情。我第一次报名学习计算机,第一次认真填表,第一次认真参评。而我来时内部传来阵阵好消息我的职称已经通过并进入公示阶段。
我做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争取上鲁院。
很多年前,当我还在涿州上班的时候,鲁院当时的副院长雷抒雁就让我来上鲁院。我嘴里说我没有一整块的时间。实际上是我虽知天高地厚、师傅重要、培训重要,但却天生逆反,不愿加入传统作家的行列。我这个叛逆的女人,我这个时代的黑马,我这个离家出走母鹿,我这个孤独游荡的孤鹰,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山鹤,我这个大巴山主峰的野人,我不仅和爸爸叛逆,和一切传统的东西叛逆,当然也和全中国的作家叛逆,和正规的作家教育叛逆,和正规的全国评奖叛逆—我在石油文协组织评奖时我就放弃过只要交作品就能得的大奖,这些年我居然从没有参加过“鲁奖”“茅奖”的评比。我自以为写作只要读者就可以了。
我知道鲁迅曾是一个时代的逆儿,可是我更认为我只有不上鲁迅文学院,才能做这个时代的叛逆儿.
我自认为我是大自然之女,就当像杨丽萍一般拒绝练功保住那种自然天性;就像唱《一个妈妈的女儿》那个梳无数小辫子的青海藏族歌手德乾旺姆一般不进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以保住天籁般歌声.
我宁愿像写出《海狼》的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一般一次一次狐独出海,哪怕我最后如海明威一般收获的只是一附巨大的白森森的鯊鱼骨。
我婉拒雷副院长的要求,是因为我要做我自己,与众不同的自己。我要向立潮头,站在反传统的风口浪尖迎风破浪,我要一个人对峙强大的中国作家团队。我要做孤家寡人。我要寻找一个支点,试试能不能撬动八千中国作家会员组成庞大的阵营。对!我要和全中国的作家对着干。对!我要向整个中国作协宣战!我要和整个中国作协的阵营为“敌”,我要向他们发起总攻。小小我要以一个人的柔弱之力和传统的中国作协在市场上对峙,我和从鲁院—中国作家的黄埔军校出来的作家团队在写作质量上对峙。
是的,我要以批判的眼光,看我自己的写作,我要警惕自己混入全中国的作家,我要警惕全中国的作家同化我,我要避免和他们清一色。我怎么能上鲁院呢?我要上了鲁院我不就和其它作家一样了吗?我要上了鲁院我还是大巴山野人吗?我要是上了鲁院我还是青藏高原原始人吗?我要是上了鲁院我还是中国石油酋长部落人吗?
就是因为我没上鲁院在写作上我才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呢!
我宁肯做一个小螳螂悲壮地以细细的手臂以小小的生命挡滚滚时代大车.那怕我被碾得血肉横飞,那怕我被碾得灰飞烟灭,
因为,这种对峙带给我无限的激情和无限快感和无边的剌激呢。我需要这个!那真的是一种向立潮头,乘风破浪的感受!
可不是?我孤独无助我独立无援!我势单力薄我孤家寡人!可是我的精神上却高度亢奋,高度富有!高度充盈,我快乐呀!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作家呀!因为我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对手那么多的"敌人"呀。
因为我没有组织,因为我不要帮助,因为我不要后台!因为我只代表我自己!因为我就是我,所以我的感受如此独特!我的见解如此特立!我观点如此新鲜!我的文笔如此流畅!我的灵感如此泉涌!就是因为我没有上鲁院呀!就如我上大学学的是数学而不是文学。我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我没有任何的思想禁锢,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如孙猴儿上可入天下可入地。
我有时感谢我上大学前从没有受过几天正规教育。
我有时感觉我上大学学的是数学!
我是大巴山野人,我是青藏高原原始人,我是中国石油酋长部落人。我要的就是这一点呀!
一个回合下来,小小的我,一个从最中国最落后最原始最封闭最偏远地方来闯京城的小小作家的书,就小获胜利,初见分晓:我的书"透明系列"销畅销天南地北,在中国引起一次一次响动,别的人出书要么自费要么只几千,而我的书每次印刷都上万,且多次再版,每次都让出版社大获全胜满意而归。这使得我离鲁院渐行渐远。离正规的作家教育渐行渐远。
而我的记者的工作对我的挑战更大,更何况我不是专业作家,我还有那么多的正事要做,哪有时间不务正业。写作也要等我这个野人我这原始人我这酋长部落女王高兴时再写。这使我这个说是知道天高地厚,其实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毛人小野小原始人小部落人,离鲁院更加渐行渐远。
直到爸爸逝世,昏天黑地后,我这个和爸爸叛逆离家出走这么多年的女儿才终于想到了回归?这中间已经哗哗啦啦地过去了多少年?这中间已经历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前年--爸爸去逝后回京,我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来了一趟鲁迅文学院。 那一次我拜见了王彬副院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表达我想上鲁院的梦想。这是我在感觉不到爸爸的愿望时第一次按爸爸的愿望行事吗?我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受中央表彰的高才生,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人大度过的。他老人家一定是希望我要既然要从事写作首先就是能进鲁院上学他老人家一定是希望我既然要从事写作首先要向中国作协组织靠拢吗?爸爸一直一直担忧的就是我创作上一直保持的大巴山野人、青藏高原原始人、精神上上游牧人、灵魂上吉卜赛部落人状态吗?
我来上鲁院,这同样是我在已经感觉不到作协对我的关爱之时第一次按雷副院长的愿望行事吗?
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这些年,我已经走得太远,根本就要游离出中国作协的视野和管辖。
我是在宣布我这个叛逆的女儿,我这匹社会的黑马,想回归一次正统?看看正规的作家院校是怎么教育作家的?
或许,多年以后,我还会突围出去,但是我这次屈服,绝对是有深刻内心原因的,绝对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
或许,再过若干年,就算我又想再次突围出去,我知道我的生命中将会因为我的鲁院经历而与前不同。我将是一个全新的我.
而我没有想到,我想上鲁院的愿望一经从心里冒出来,就如搬开了一个清泉上石头,那泉水一下子汩汩涌流出,一下子漫天漫地,淹没着我,那海潮,一瞬间便轰轰隆隆,带出山呼海啸。似乎我不马上去上,我就会死掉。而我更没有想到这愿意一经我的口表态出来,我便显得那般不屈不挠,那般百折不挠。
我跑去见中国石油文协的北原和安琪,表达了我的想上鲁院的愿望。可是去年的通知下来了,却只是一个青年作家班。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不甘心,还是想上,决定冒进。总感觉如果我不上就再也上不上鲁院了。就好像我不上鲁院我就从此再也当不成作家了一般。
我拿着鲁院的通知书上蹿下跳,我找报社人事张文业、中国石油报社副社长邱宝林、社长白泽生一一签字批示,我找人事处杨文清盖章,我送交文协请北原盖章,总算是批下来了,我又关照文协安琪邮寄情况。中国石油文协把我的表报到鲁院了,我的心却揪在一起了,我担心批不下来,因为我已经过龄,其实我也不愿意和“八零后”在一起学习,可是为了上鲁院,我没有办法,只能背水一战。还好,中国作协批下来了,鲁院也通过了。正当我高兴之时,没想到我高兴的太早了。白描院长有一天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和我商量一下,和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的、陈忠实作家推荐的、八零后小姑娘换一下,让我明年再上。白描院长亲自给我商量,我只好答应。
明年再上?我虽然答应的白描院长,但感觉却很绝望。明年我真的能上上吗?可是既然我想上,我就一定要争取。我仿佛在做人生第一件实事。我仿佛从来没有这么拗过。
今年新年一过,我就瞄上了中国石油文协的北原和安琪,吩咐他们鲁院通知一来了就告我。我就瞄上了鲁院的白院长,跟踪鲁院下通知的进程。我甚至想给铁凝金炳华陈建功等打电话。通知终于下来了,我又是一番上蹿下跳,在中国石油报邱宝林、张文业、杨文清,北原、安琪的齐力热心帮助下,在白描副院长、王彬副院的关照下,在严迎春等老师的努力下,我终于如愿。
这会儿,我这个相信天缘的人,第一次想起著名作家文洁若给我题的字:“事在人为!”
我知道,竹子上鲁院和别的作家上鲁院一定是不同的,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竹子是野人。野人上学本就是一件稀奇事情。野人上正规学校那更是一件稀奇事情。野人上作家的黄埔军校那更是天地间一件稀奇事情。
我和鲁迅先生好像有缘
饭后,我在鲁院长方形的小花园中转了几圈。这小花园虽然幽,但却不够深;虽然雅,但却不够致。只有那个亭子古色古香,那段宫墙优雅幽静。亭子被竹子掩隐,宫墙被松树环围,在京城显得非同一般。我忽然想起绍兴的鲁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