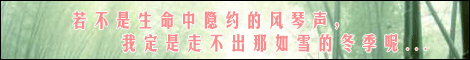那时我上初中,有两个中学同班同学,其中一个叫卓玛(化名),她的妈妈后来是民院的副院长,再后来她的妈妈是青海的副省长,她的爸爸是“青干班”的学员,也是个正厅级。上初中时,放学上学,我经常与卓玛走在一起。这个藏族姑娘不 知道为什么与母亲的关系非常非常“远”。每天与我谈话的内容就是一个,那就是数落她的妈妈。
她家那时住在三栋学生宿舍最南那一号楼。由把头几间对面宿舍改成。而我每次去找她上学,敲门后让进来,小心翼翼推门进去,其母总是像一个女皇坐在铺满藏毯的“朝廷宝座”上,很是高大威严,不苟言笑。我总也是轻手轻脚地溜入边房,叫上卓玛,然后我们一起蹑手蹑脚地溜出来,沿着墙边儿走,走呀走,总也是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笑声才能爆发出来。
有一次到十里铺大队学农,我与她住在一张炕上。有一天半夜醒来,发现卓玛的眼睛是半睁着的。我以为她醒着,便与她说话,可是她却没有反应。我喊她,她也根本不理我。原来她是睡着了仍半睁着眼。这可真是吓人!整夜睁着眼睛睡觉。我害怕,但不敢说,怕伤她自尊。有一天,卓玛问我:我晚上睡觉不闭眼睛,你害怕吗?原来她有“自知之明”。原来卓玛根本不忌讳,经常对同学们说她晚上睡觉不闭眼睛这件事儿。我们住的院子是农村干打垒的土庄廓,干打垒的土房子。正房正头一张老人家像下面一个米柜子。我俩住的这间房子在正房的右边土炕上,正房左边的房子里放着房东的两口子两个巨大的棺材。我本来胆子就小,又爱胡思乱想,更爱联想幻想。怕棺材又想听与棺材有关的恐怖故事本指望与卓玛住在一张炕上,可以减少恐怖,没想到这丫头居然是睡觉不闭眼。我只好转过身子背头她睡,强迫自己晚上不看她,且命令自己不多想。
我的高中同学孟玲
其中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叫孟玲(化名)。她的爸爸当时是青海民大军宣队的头,大家都叫孟团长(化名)。想想一个团长本就一个小小处级,那会儿却是管着青海民大的所有人。这个处级管着青海民的那么多的厅级干部、活佛、王爷、全国重点高校来的教师,当然还管几千各民族藏、蒙、萨拉、回、土、维吾尔、朝鲜、哈萨克等民族的少数学生。甚至兼青海民大的党委书的副省长韩洪宾如果驾到都归孟团长“管”。就连原党委、后G委会、工宣队,都要听军宣队孟团长的?也就是民大两派闹出了名,先进了工宣队,后进了军宣队。也就是工人和军人都进来管大学了。按理孟团长不过一个处级,而青海民大除了兼任的副省级韩洪宾,还有李民新好像也是副省级?厅级可就多了,副处更是多了。因为六栋教师楼,有两座就叫教授楼或处长楼。再加上没有住上处长楼的处级,青海民大的处级更多。可是孟团长这个处级就不一样,光警卫就好几个,还可随时调动部队。更有孟团长的政治地位更是重要。
为什么要先工宣队后军宣队入驻呢?当然是民大的武斗太厉害,“2.23事件”死270多人,民大学生冲在最前头,多亏那天是后门开射。“2.24事件”死伤九人,这在中国高校少见。更有民大两任院长相继自杀身亡。后一个戴院长自杀后,两派疯狂武斗,卫生室居然成了“重庆渣滓洞”,民院武斗的疯狂震惊了中国高层与青海高层。有一段时间,上层动怒,把几千学生遣散回牧区农业区家中,有一年,民大甚至被降成中专,轰轰烈烈的民大一时间人落马稀风声鹤泣。一时间,热闹的民大变得戚戚惨惨冷冷清清戚戚。一年后,才又恢复青海民大。而军宣队的入住就是在这个环境下。
第一次知道孟团长一家,是有一次妹妹小美拉与小朋友们去办公楼去玩。当时是放暑假,办公楼里冷冷静静,空无一人。空无一人,楼里就显得凉快湿润。妹妹们楼上楼下串来串去,她们并不知道四楼住有孟团长一家人。等妹妹们玩够了,需要离开时,几个警卫却是堵住了妹妹们,不让她们回家,说是孟家人把房门钥匙丢了,一定要找到钥匙,才能放妹妹们回家。因为孟家搞不清楚钥匙是不是被妹妹们捡到了。捡到了不交或是扔掉,这可是大事儿,弄不好就是JJ斗争,弄不好就要上纲上线。如果是其它小孩子把钥匙丢了,属于孩子天真浪漫无心无肺,可是如果我的小妹妹毛美拉把钥匙捡到又丢了,那可是不得了,因为爸爸的家庭成份不好,又是被打倒又“畏罪上吊自杀院长高参”。真不知道等待小妹妹的毛美拉的会是什么。孟团长一家当时在民院的地位,那可是了得!
我们在家里等小妹妹毛美拉回家吃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们于是分头去找小美拉。我终于在办公楼的一楼警卫找了妹妹们。只见几个小女孩子,都被警卫命令蹲在走廊的地上。像将被抓进监狱的小犯人。警卫们并没有捆她们。可是这几个小姑娘都不约而同地把双手合拢特别是大姆指合拢,似乎被一个一个又一个无形的手铐铐住。几个小姑娘显得那么瘦小柔弱那么绝望。特别是我的心爱的小妹妹毛美拉。毛美拉的眼睛本来就楚楚动人,特别一对眸子,幽深黧黑渺远忧郁。此刻毛美拉的双眸子,平添了更多的无助与迷惘。幽怨与迷惑使得她的神态中多了几分儿楚楚动人,真是令人我见犹怜。我哪敢质问警卫,更不敢反抗。戴院长上吊自杀后,我们一家人就成了造反派批斗游斗围追毒打的对象。我怕我反抗会给毛美拉添更大的麻烦。我更怕我的一时冲动会弄丢我心爱的小妹妹。那时候,从大巴山老家不时传来消息,因为高成份,毛家的好多重要亲人都一个一个以离奇方式消逝了。奶奶站着逝在潇湘竹园、堂二伯毛高济与三姑夫两拉到大树梁砍头,二伯毛高圓被枪毙尸体都没有收被滚滚汉水冲走的...............我不是这会儿才恐怖着小妹妹会不会逝掉,而是随时恐怖着我家几人会不会逝掉。我不是那时才特别地想到了生与死,而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生与死这样的大课题。现在想想太不可思异了,一个小屁孩子小姑娘居然时时刻都在想生与这样的大课题。现在想想太不可思异了,一个小屁孩子小姑娘居然时时刻都在生与死的恐怖中沉浮。不仅仅是我,我的姐姐毛美睫,那时才多大,天天思考这些沉重的话题,以致额头上都出现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年过去,现在的姐姐现居然比少女时的姐姐漂亮一万倍。那时我爸爸毛高畴妈妈徐馨儿天天沉浮在生与死的刀刃上不说,连我们三个小小的姑娘天天都是走在生与死的刀刃上。当时的中国社会按成分被划成好多类,就如印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而我们家庭成份是最下层。可是我们绝不是真正的贱人,我们更像是原人的大脑,整天思绪纷纭,整天感情丰富,整天思虑多多。我爸爸太优秀,又站在中国成份最上层:爸爸的成份是革干,又是部队红人“出生”——毛高畴背叛了家庭,六亲不认,双亲生死不顾,母亲为其自杀,父亲为其郁闷而逝,毛高畴却把一腔深情寄托在部队,把部队当父母亲亲。毛高畴以家庭成份那么不好,还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且是学马列的。正因为此成为青海各部委各厅级单位争的香饽饽。可是爸爸人大研究生毕业后却坷坎重重。先是在民林厅卷入两厅人夺权争斗,卷入桃花案;被西北王要去西安当秘书,又被青海方抢回来,又被青海民大抢来,却又成了自杀院长的高参。又被保皇派推为的政委。爸爸一个人的风雨沉浮刀刃生涯,也带着我们的母亲与我们三姐妹沉浮风雨雷电之中。
说实在的,那几年,我那么小,却已经为了亲爱的妈妈徐馨儿的生死,为了心爱的小姐姐毛美睫的生死,与心爱的小妹妹毛美拉的生死,当然还有我自己与爸爸的生死,时刻担忧。我一次一次关注那些与家庭决裂的勇敢者们。叛逆中离家出走的清醒者们。那些揭发父母致父母被枪毙的大义灭亲者是我的格外关注。那些与父母划清界线且勇敢加入批斗父母行烈的红人是我的格外注意。特别是忆苦思甜进入高潮时,我想过一千一万遍。可是我太重感情,我知道这样做对重感情的爸爸是致命一击。我知道对方打不倒的毛高畴,我这样一做就可轻易打爸爸打垮或是击垮。我知道这样说不定我们四个保不住,我更会丢了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不能!不能!我绝不能做那种丧天良的事儿。可是我如何向m老人表达衷心呢?我如何向组织表衷心呢?我如何向同学们证明我的衷心呢?
我们姐妹三个都心里充满怨悔。凭什么?大巴山的亲人我爷爷家有乱石镇大商号,我的奶奶的父亲覃有370担课土,我三姑夫是高桥首富,我的二伯娘是瓦庙贺四大房.........但是我们从生下来都没有见过他们,特别是我是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爷外奶的小野人。他们富不富他们有没有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凭什么?爸爸掌柜子不当,带大巴山百多美少年参军,动员家里交田交地交商号,他们才是真正的革自己家族命的革命者。他们参军不是为了追求利益,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是普度天下劳苦人民的善心。他们才像是真正的革命者。更有,凭什么?我们三个女儿都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们凭什么要为爸爸的剥削阶级家庭背黑锅?我们那么小凭什么你们大人之间的派性斗争,却把整个民大两派武打的焦点吸引到我们三个小小人身上?
我们三个又没有参与你们大人的武斗,造反派的头儿们,那一帮智商高高的权谋高手,凭什么组织自己的孩子追打我们三个小姑娘?凭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助毛美拉,小小的毛美拉,可怜的毛美拉,无助的毛美拉。我表态可以扣押我,让小妹妹们先回家,可是警卫们不同意。脸上冷如冰霜。我只好也加入蹲在地上等待“宣判”等“判刑”甚至等待更可怕什么事情的小妹妹们的行列。我安慰自己:军宣队是进青海民维持持续的,当不会如想的那么严重,他们当不会乱来。可是我是在惯性思维中无法解脱。生与死,死如生,又一次如雷电交加轰呜在我小小的脑袋中。我想万一我们一起沦落,我能不能学刘胡兰一样,虽然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学刘胡兰。但是我怎么样我可能去经受,可我舍不得我心爱的小妹妹毛美拉受一点点惊吓与磨难,更不忍心让她忍受一点点死亡的恐怖。
我先也不自觉地合着双手,像被什么铁手铐铐住一般。接着,我挣脱了这个姿势,双手抱着头。我听到更多部队战士涌进了办公楼,我听到楼上楼上都有战士的寻找的脚步声,我听到民大的广播喇叭中反复出现着武小安妈妈那温柔好听的声音:哪位师生与孩子在办公楼捡到一串钥匙,请火速送到院办!那声音余音袅袅,翁音幽幽,在布满了死亡恐怖的夜空中,像一种我们这帮小孩子求生的救生网,但是瞬间又破碎了,消逝了。我们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我们在死亡与被救的期望中彷徨。
我与妹妹们就这样,等待着的恍惚是“入狱”或是“死刑”或是“更恐怖”的宣判。
那是八月放暑假期间,我们都穿得比较单薄。可是那办公楼本来就阴渗渗的,凉浸浸,现在更加阴森恐怖了。西宁的温差本来就大,太阳一落,我与妹妹们就显得衣襟单薄就显得“阴处不胜寒”。可是孟团长家的钥匙怎么还没有找到?
而我是不敢说,从来我的大脑中就有自己的思辨能力。我在想一个问题:你孟家人是个什么家庭?你孟家不慎将钥匙丢了,你有什么权力把我的妹妹们全部“扣押起来”?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从下午到深夜。妹妹们个个涉世不深,如果捡到钥匙,一定会说,怎么可能不说?再说丢一串钥匙,怎么弄得这么恐怖?如果真有“坏人”想破坏军宣队进驻,怎么会派这么小的女孩子施行?这也不可思异了!更何况,那一派最怕的可是我爸爸派出我们家人,可是连我都不知道,小妹妹毛美拉怎么可能知道任何?妹妹们那么单纯幼稚,根本不可能撒谎。就算你们怀疑,她们已经说了都没有捡到,你们有什么权力“羁押”她们。她们还小,实在不行,你们就羁押我吧。就算这钥匙再也找不到,就算要羁押或是处死,这么小的妹妹们也当赦免吧?
一时间我思绪纷纭,可是我不敢说。自从运动开始,我爸爸被推为保皇派的政委,我们家姐妹三个就成了造反派近百十个男孩子甚至十几个女孩子追打的主要对象——打得最凶的有二十几男孩子加几个女孩子。虽然是两派,但保皇派这一派根本就是原来的党委一帮人,文明儒雅,师道尊严,多是中国名校高才生,多是自愿支边,多是一腔热血来青,根本就不会打架。更何况,青海民大的两派,造反派是先成立的。斗争已经激烈,这边还一团散沙,正是为了应付“破坏教学”“使教学难以为继”那一股力量,那一股山呼海啸般的力量,老师们才自发地要成立一个组织应付一下,目的只是为回归正常教学秩序。青海民大的教师都知道,毛高畴是戴院长抢来继承温志忠书记位置的第一人选,所以才联合推举毛高畴当保皇派的政委。这保皇派与造反派是后来才分出来的。当时青海民大毛高畴这一派叫延安民族战斗团。青海民大造反派叫十一民族战斗团。保皇派就算是揪斗过省委副书记韩洪宾也是被迫的,也讲理文斗——运动一起,造反派号召几千字生包围省委,逼韩洪宾改口否则就要揪斗韩洪宾,韩洪宾被逼无奈,只好违心“抛下级保上级”,韩洪宾同意“撤销给戴院提的那一级”“同意造反派揪斗戴院长”。青海民大的教师学生一听,不干了,蜂涌而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韩洪宾,不是人身揪斗,而是想让韩宾宾改口,回归正义。因为这事儿,毛高畴也承认:我也干过亏心事儿。但那是被逼无奈。因为韩洪宾自己也承认他是违心的。我们只是想他改口。
而青海日报死造反派三百来人,是部队开枪,抓青海民大五十多人,也是省里还是省军区决定,与青海民大的保皇派无关。可是案子翻过来,造反派那帮可不似有教养的保皇派,他们不是打砸抢分子,就是“身上长刺,头上长骨”野心家。把卫生室弄成“重庆渣滓洞”就是造反派一帮人干的。老虎凳、铁鞭子..................谁也想不到疯狂的打手居然也可以是大学的老师们。民大的孩子也被分成两派卷进了武斗。保皇派不可能组织大人或小孩子去打造反派家的小孩子。可是造反派那一派可就不一样了,有锅炉房工人的孩子,有后勤干部的孩子,有食堂职工的孩子,更多的是草原上聚集起来的野心勃勃的原始人——少数民族学生斗争保皇派的阵式是最最吓人的了,他们中好多甚至听不懂一句汉话,几千人的批斗会,只要有老师用藏语或是蒙语或是其它语言煽动一下,说这些是什么什么坏人,这些单纯的学生就冲上去把老师们掌打脚踢往死里打。而造反派这些人好多都是部队一军或是一野转业的军人们的后代。更多是中国反骨发达的野心家。他们是最有战斗力的一帮人。他们是寻找战场的一帮人。“老子英雄儿好汉”!他们的孩子们当然也是特别能战斗,组织起来特别能打人。他们的激情与热情本来就没有地方宣泄。而他们打的对象,那段时间,整个民大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家姐妹三个。因为戴院长已经畏罪自杀后,他们首先要整倒的是毛高畴,这个院党委的成员,这个戴院长的总秘,这个保皇派的政委,这个对立派的灵魂人物——文革前期,青海民大除了出现过101张大字报,还出现了一张轰动青海省的漫画:漫画中院党委五人抬着胖胖的戴金璞院长,毛高田(笔名毛高畴)这个四眼位置最突出,拿着一个气筒在给戴院长打气。由于打入的气太多,戴院长的身上都破了,无数气流从身体上冲出来。漫画上,毛高田的衣服被画成一个天蓝色的中山装。毛高田的名字被篡改成毛高天。从这幅漫画,就可知道造反派为何在戴院长自杀后,为什么要整毛高畴了。
争夺青海日报社的“2.23事件“死270人伤几百人,平息青海民大两派火并的”2.24“事件死3人伤六人,让青海民大的两派上升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清明节,造反派押着保皇派的头头们去南川烈士陵园,那里面埋着273位以上“2.23事件””2.24事件“的死者。造反派押着保皇派头头们给这273位死者叩头。多恐怖呀,273多位死者,要戴院长与爸爸一一叩过来,头咚咚地被造反派押着向墓碑、向水泥墓基撞去。戴院长与爸爸都叩得额头上鲜血长流,几次休克。然后参观成果展览,非要让保皇派头头们跪着进展馆,跪着上楼梯,戴院长与爸爸等又跪得膝盖上鲜血长流。多少次大十字、西门游斗结束,戴院长与爸爸等已经走不回去,只有往回爬。戴院长渴得不行,造反派就把戴院长的头押进臭水沟喝水。
当然造反派同时想整民大党委其它成员,特别是雷惊物。毛高畴与雷惊物这两个人,毛高畴是“高参”,雷惊物却是“高参”的实施者。更有雷惊物是毛高畴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先把这两个人物整自杀。雷惊物是老青海民大,属民院元老,扎根已深,关系藤织,且是也是部队上来了,所以造反派感觉难以下手。造反派是在卫生室设“渣滓洞”十八般刑具统统用上审讯保皇派的头头们。可是他们还不敢公然整死这几个人。最好的是让保皇派的头头们都自杀、特别是毛高畴,这个骨头铮铮的保皇派魂魄。只有毛高畴自杀了,保皇派的魂魄才真正被打散。保皇派才能被击破。只有先让毛高畴自杀,才能开啃雷惊物这个硬骨头。开整其它的保皇派成员,才能把原来青海民大的党委班子彻底打垮。
造反派虽然已经暂时得势。但是造反起家的人心是虚的。他们原来多不是院领导,造反起家,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是造反起家,他们是打砸抢坏分子。他们是投机主义者。他们是趁乱打劫孤机会主义者。成立青海民大G委会时,心虚的他们拉来几个中立的准副厅类,青海民大掌实权的几个中立的处类,充实进来,只是为他们自己壮胆。他们知道,他们得胜是暂时的,是自己遥远的大头们的一时糊涂,等大头们清醒来,他们就被再次打回原地。他们失败是永恒的,是不可能被历史改变的。他们知道,他们终将订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可是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他们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伤害的人太多了。他们伤人伤得太深了。他们的手上已经有人命了,他们已经逼死了戴院长,他们与保皇派的斗争已经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他们最害怕的最恐怖的是中国上层再一翻,原党委势力没有被彻底打垮,保皇派再翻上来,会来报复他们这一帮造反起来成为新领导的一帮人。他们太清楚,兼民院书记的省委副书记韩洪宾虽然在被静坐围斗学生的逼迫下违心同意批斗戴院长,可是韩省委副书记是被强迫做出的违心之举。他们知道,韩省副书记如果没有受到挟持,十分欣赏的就是戴院长,十分喜欢的就是毛高畴。这一点,造反派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知道,那一次保皇派被激拉出韩宾洪斗,毛高畴出现,不是去扩大态式,而是去保护韩洪滨的。虽然选反派离间了他们三个,可是他们三个在维护青海教学稳定上是共心介力的。已经翻过一次了,那一次“2.23事件""2.24事件"后,上面先表达是保皇派正确,青海民大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省里还是军区决定抓了青海民大五十来人(待核实)。听说J老师被抓,关进看守所,吓得把尿与屎都撒拉到裤档里了。”
而抓这五十来人时,戴院长还保了他的生活秘书傅xx——我爸爸毛高畴是党委秘书,也就是民院的两派的头儿是戴院长的两个秘书挑头。先是自认为失宠的秘书傅xx成立了后定的造反派,接着被认为得宠的毛高畴成立了后定的保皇派。当时两派都不肯承认自己是保皇派,因为上面提倡造反,因为大人物提倡造反。毛高畴这一派是戴院长在某个关键时刻一定要跳出来,才成为保皇派的。造反派的头头某某。有人说是戴院长是担心某某知道太多。但是我爸爸对我说:戴院长这个人是出于善心才保他。可是他不领情。特别是后来造反派又翻过来,某某又失去了造反派的信任,某某在孤立无援彷徨无助,以对戴院长更加残酷无情还表达对造反派的忠心。
2.23事件""2.24事件"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后,北京来西宁串联的学生,好多死在青海日报社。北京学生的家长不服,状告中央,中央调查驻守卫青海日报的造反派学生真的没有枪。当时青海军区原副司令、主张开枪打占领报社学生工人的赵永夫押着原青海军区司令刘先权到京西宾馆开会,刘先权正在台上介绍枪杀反革命学生的经验,风向突变,赵永夫被逮捕,刘先贤被释放。青海方风云大变,又给青海民大造反派平反。造反派一上台,就把保皇派与中国的“二月逆流”案强拉一起。就开始在卫生所私设公堂,十八般刑具皆上。毒打保皇派头头与院重要领导们。他们准备把更多的保皇派送进监狱。送监狱的名单报上:“戴金璞、毛高畴、雷金物、杨玉局、郭天德..............”更多的老师被整或挨整。可是光被整和挨整不行。恐怖中造反派希望原党委的成员与支持者一个一个自杀,那么他们心底的恐怖才能真正解脱?因为两派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已经出现人命,两派斗争已经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已经不可以和解,已经永远不可能调和。造反派对保皇派的批斗已经无所不用其极。造反派害怕保皇派哪一天翻过来,也受到同样待遇,后来,戴院长自杀后,他们又担心追究戴院长自杀责任,更担心丢官。一句话,青海民大的两派斗争已经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造反派中一些高智商,在卫生室把保皇派的头头往死里打,但是却不敢真的打死,他们要原院党委的成员、原民院的要员一个一个自己自杀。就如上吊自杀的戴院长一般,他们好一次一次开庆功会。庆功戴院长上吊自杀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毛高畴了。
怎么样才能让毛高畴自杀呢?造反派一帮人收集的信息集中到一起了。造反派的政委傅xx也在人大进修过,对毛高畴做了深入了解。毛高畴这个精瘦的知识分子,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可是,是人就有弱点。毛高畴太重感情。就是因为太重感情,毛高畴是大巴山那一批参军青年中唯一一个当了军官又没有与娃娃亲妻子离婚的人。是55师转业军官中少有的几个没有找城里姑娘再婚的乡愁色彩浓浓的人。因为在乎徐馨儿是为“其自杀母亲”最爱的准儿媳妇,毛高畴居然舍弃了追他的人大本科生大姑娘张某、大将的女儿张某、爱他爱得要死的人大校花张某。就是因为太重感情,毛高畴的母亲自杀后毛高畴一病不起,眼睛哭出血。就是因为太重感情,父样“与其呕气病死”后,毛高畴得了肺结核,多亏张姑娘精心爱守,才没有倒下,才顺利毕业。更有人注意到,押着毛高畴一帮保皇派的头头去西门口劳动改造,可是毛高畴每天中午要来回骑行三十多公里,只为家里三个女儿要吃中午饭。二女儿常流鼻血,毛高畴被打断腰锥未愈的前题下,仍骑行来回五十公里到二十里铺给二女儿治流鼻血。这帮人了解到,毛高畴最喜欢自己的三个女儿,在外受了再大磨难,可是回家看到三个女儿,心情就会好起来。这帮人了解到,毛高畴最为三女儿的出色而自豪。因为大女儿多次评为三好学生,中学就让入党;二女儿会讲故事,学习拔尖,学校宣传队主角,体育破多项校纪录。小女儿更是聪颖灵秀可爱天真,两只眼睛深幽幽、毛绒绒,憨墩墩,真是心疼死了。更有专人深入大巴山毛高畴这个多愁善感的人其大巴山的上辈同辈直系亲人已经一个一个消失。他的亲人,只有一个幺姐还活着,剩下都是他不熟的后人。幺姐年龄大了,如果让他失去三个女儿,毛高畴一定生不如死。造反派头头一帮人观察来观察去,商量来商量去,把目光对准了毛高畴的三个女儿。有说恐怖是杀机最深的源泉。造反派们虽然得势,但是他们有预感,总有一天,他们这些破坏教学秩序序、打砸抢无恶不做的投机分子将会被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决不能让保皇派有翻身的机会。决不能!坚决不能!!!他们要让保皇派当翻身时,主要的知情人已经从世界上消逝。他们巩固他们得之不易的权力,必须把青海民大原党委成员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踩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造反派们心里都有了一种默契。造反派的头儿们都知道,出手必须要快,要在他们掌权的这几年,快快把保皇派的要人处理掉。不能让这些埋在青海民大的定时炸弹某一天爆炸。炸到自己或炸到自己的亲人。自己或是自己的亲人毁灭,这是造反起家的几个头头最不想看到了。造反派的头儿们有意无意地暗示甚至组织自己的孩子们去打毛高畴的三个女儿。难道造反派们找到了让毛高畴自杀的最好的入口:先打残甚至打死他的三个女儿,先让他生不如死,然后再一步步促成毛高畴自杀...............
让毛高畴自己解决自己,就如让戴院长自己解决自己一般...................
运动中期,对于造反派更有可怕消息,保皇派仍在挨整,可是青海省委把提拔毛高畴的当青海民大实际的党委书记的事儿就放在案头。因为毕竞,毛高畴太优秀了,即是55师163团政治处的党的可靠干部,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高才生。青海民大的书记没有比毛高畴更好的人选了。再说,毛高畴在民院的内乱中,起到很好的维护持续的工作。保戴院长、暗保韩洪宾,青海报社日报"2.23事件"暗救造反派多少学生的命,“2.24事件”民大死伤九人落实与毛高畴无关,毛高畴领导的保皇派从没有乱来。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提拔毛高畴的事件,再一次提到了省委桌案上。省委先让毛高畴当民大扎尖农场的书记,调查组再次深入大巴山。只等调查组回来,毛高畴的提拔就将顺利推进。这对造反派却犹如晴天霹雳:毛高畴提拔上去,对于我们造反派那可了得?
毛竹也是想了好几十年,才明白后来附中班主任与教导主任与好几位任课老师联合批评自己的原因?如果不是政治原因,凭什么那么老师像发了羊羔疯一般联合起来整一个并没有犯任何错的小姑娘毛竹呢?如果不是政治原因,凭什么那么老师像得了狂犬病一般,联合起来咬一个全校公认全面出色的小姑娘毛竹呢?
毛竹也是想了好几十年,才明白,为什么那块飞石差点要了自己的命,自己差点尸横上学或是放学路上。
毛竹也是想了好几十年,才明白,为什么爸爸那一次差点淹死?爸爸的提升引起了多少人的恐怖。
与造反派相比起来,造反派的小孩子们反而比较单纯。他们就是想表达自己的革命热情。那时不是强调JJ斗争吗?如果是JJ斗争,那就因当寻找敌人。他们就是打敌人,他们就是想发泄,他们的目标是原青海民大党委几人。打大人他们不敢打,打小姑娘他们可是拿手,特别是一群人转打三个弱小的小姑娘,那可是开心又愉快的事情。于是他们无意中按他们父亲们的暗示或是指使围打毛高畴的三个女儿。他们几十个男孩子精干精瘦,像游击队一般在民大与民大周边神出鬼没,特别能出击,特别有战斗力。他们中有的个子已经与大人一般高了,有更多已经与大人肩膀一样高了。那一段时间,整个民院那么大,几十个男孩子伏击打击摧毁的目标居然就是我家姐妹三个。
常常的毛家二个小姑娘正走着(小妹妹太小,常不用出门,常在妈妈的保护中),忽然一声口哨声,如天空中掠过一道凌冽的风,一大帮全付武装的孩子就如天兵天将出现了,他们的速度居然像子弹一样快,他们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拿着石头,有的举着鞭子,有的拿着拳头。他们如沙尘黑暴一般包抄过来,把毛家两姐妹轮番猛击狠打,打得稀巴烂,如两朵残红败叶,瘫在泥水中。
多少年以后,也就是今年,我看电影《无问西东》,我看到青华大学那一帮大学生,一帮高大勇猛的大男人,所谓的中国知识精英,被什么力量洗脑,无中生有,围殴毒打一个柔弱纯清天真靓丽的少女,让少女成了坟墓中的活鬼,丑陋的不能见人的活鬼。原因仅仅是因为少女打抱不平,无意被冤枉,以为她插入了老师的家庭。原因仅仅是少女太崇拜当时的领袖欺骗大家说自己见到领袖大人——本来那机会就是她的,可是她那天感冒了。就在电影院,我泣不成声。回到家里,我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我终于哽咽出声。我知道,我是哭她,也是哭我自己。是她的遭遇唤醒了我的记忆。那些年我哭过多少次,眼睛都哭成了孙悟空的“永不褪色的红眼眶”,可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被围打被围批哽咽出声过。我不能出声,我不能让爱我的父母听见!我更不能让“压力下额头已经出皱纹”的姐姐听见!我不能让心爱的柔弱的小妹妹听见!我不能让民大那帮虽与爸爸一派但却不肯伸手帮助我们三个小姑娘一下的所谓同伙们战友们听见!我更不能让造反派的那帮打手们权欲狂们听见!多少年我都在学习忘记。多少年我在刻意学习忘却。多少天我在刻意学习忽略。以致我的大脑中常常出现大段的空白。
可是,现在不行了,《无问西东》中少女的被围打,大震撼我心了,它唤醒了我的记忆,让我退成空白的记忆“昨日重现”。我这才发现,那段时间的恐怖与惊惧与无助从来就没有消失,那段时间的生与死刀刃上行走的无助与彷徨与绝望从来就没有消失。它们一直藏在我的生命中,一个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就如我头上的骨错位的伤口,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我的头发中。
都怪爸爸刚调到民院,居然是自杀院长的“高参”,保皇派的政委。爸爸带着一千多师生要和造反派一千多师生斗,那分明就是一帮原始人,那分明就是帮野人,却全然不想自己家里没有儿子,三个女儿就成了造反派共同打击、首要打击的对象。
已经多少天了?已经被打过多少顿了。我真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觉得天地间恐怖无所不见。多少次放学站在八一路小学的泥泞中不敢回家,只有等柔弱的妈妈来接。爸爸已经被打昏过多少次了,多少次被送医院,根本自顾不暇,身上的军大衣常被撕成条条。多少次与姐姐走在路上,忽然一阵凛冽寒风倏然刮来,一帮男孩子就像阴冷中射出的炮弹,向我们姐妹两人合围而来。有一次,在民大,那帮男孩子正在疯狂围打我的姐姐。会出人命呀!我姐姐会被打死了!好几个邻居老师从身边走过,我和妈妈与无助地求救邻居,其中有一个邻居居然是毛家自认为关系最好的邻居。其中有两位居然是毛高畴认为最铁的“战友”。居然没有一位邻居教师一位“战友老师”敢冲上去劝架或是打抱不平。让我们耿耿于怀的是,其中有两位居然是爸爸一派的,还是爸爸一派的骨干,可是他们却绕开了。他们太明白了!他们都知道劝一个架,得罪的却是整个造反派组织一千多师生,谁也不敢冒那么大的风险。每天晚上,都有敲玻璃的,打门的,甚至硬要闯入的。有些男孩子甚至把大字报贴到我家门上窗户上,甚至把赃东西弄在我玻璃上门上。啥叫“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啥叫“十面埋伏”?我算是领教了。恐怖就如魔鬼包围了毛家,死亡的影阴不知道何时笼罩着青海民大。
多少次半夜我蓦然醒来,爸爸根本没没睡,只好站在窗户前,骂那些埋伏在窗外向我家暗中射石头、偷偷打弹弓的“大小敌人”。
恐怖中,最坚强的居然是我的妈妈徐馨儿。有一次,几个造反派的娃儿,在大人的指使下打我姐姐和我,妈妈与窗户内观看助威。妈妈大喊:你们别怕!冲上去!打伤我负责!那一次姐姐和我两个人对付好几个男女娃儿,居然打了一个平手。当然主要是姐姐的功劳,我太柔弱了,几个轮回就被打倒在地,我爬起来跑了。
事情的转机有一天,造反派的二十几个男娃儿在汽车房的路上冲上去围打我的姐姐。我的姐姐终于知道了民大没有任何人可能帮助她。我的姐姐知道,就算是我与她一心,可是我打仗根本不行,一个是我身体柔弱一个是我根本就是一个只愿幻想不愿争抢的人,打架指望我那可是天方夜谭。孤立无援的我的姐姐终于知道爸爸妈妈邻居组织学校都不能救她。姐姐终于明白只有靠自己。姐姐终于明白了只有指望自己。姐姐终于不再指望任何人出面帮助她。姐姐可能又一次感觉到死神已经降临。绝望中姐姐豁出了。姐姐的耳畔响起妈妈的话:你们别怕,冲上去,打伤了我负责!绝望中的姐姐忽然间成一个小斗士,在二十几人的手中疯狂挣扎,来回冲闯。那时候,青海民大六六栋老师楼前到汽车房没有任何建筑,是两块大大的台地,上一层种的是青稞,下一层种的是麦子。两层加起来足有好多亩。姐姐与那二十几个男孩子的战斗太惨烈了,从上台阶这头滚到那头,从上台阶打到下台队。压倒多少庄稼,粉碎多少种在塄坎上的野牵牛花。远远的看去,就如二十几只恶狼想咬一只小鹿。他们滚呀滚,黄尘被滚起来,更多造反派的孩子们加入进来。最后干脆看不到人,只看到一个巨大黑影在滚。如同一群疯狂的马蜂,在叮咬一只可怜的小小翠鸟儿。姐姐可能是感觉到了死神的驾到,恐怖到了极致,姐姐豁出去了,挣扎冲闯中姐姐的脚踢到了其中一个男娃儿的小牛子。那个男娃儿大叫一声,蹲下来捂住下身,然后在地上来回翻滚,毁坏更大片庄稼,发出被杀猪一般的嚎叫声。那声音可谓惨绝人寰,惊动了其他几十个男孩子打手。他们都放下我姐姐毛美睫,围过来救他。我的姐姐就这样解脱了危险,逃脱了死亡。从那以后,男娃儿们打我们姐妹三个的阵式松下来了。他们实在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女娃娃,逼到尽头,生命中居然能爆发出那么大的力量,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恐怖。不是对少女身体的恐怖,而是对一个小小少女精神的恐怖。这小小少女精神的力量让他们心惊胆寒。他们怕丢双蛋,他们怕伤牛子,让对我们三个女儿打得轻些了。
说实在的,总也是不知道哪一天会被打死,哪一天会被整死。似乎死的结果是定了的,就如我大巴山的直系亲人们,他们一个一个都被整死了,我们也会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死。我已经被他们差点打死一次了。我已经差一点尸停附中上学或放学路上了。那一次飞石离我的太阳穴只一寸。只一寸,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已经得成了。我知道我只是侥幸没有死。我预感他们不打死我们是不甘心的。我知道我早晚会死。但是我不能容忍,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对付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小妹妹。
我一直是在恐怖中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这种恐怖一直持续到我爸爸调出民院:爸爸看我体育成绩出色,为了我成中国体育人才,爸爸选择调到了青海省体委。这种恐怖一直持续到我跟随体委子弟到互助下乡,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
正因为是在这种情况下,明知道为了孟家丢了钥匙他们不当羁押我的妹妹们,但是仍是默默承受这种“无理行为”甚至是“非法行为”。其实我心里明白,那时候,哪有什么有关这此小事儿的法?只能默默忍受承受。唯一祈祷的是,但愿我与心爱的小美拉等妹妹们能平安走出这座冰冷的办公室,能回到家里吃上妈妈做的热饭。
还好,终于有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走过来了,说是钥匙找到了,说是把这些小孩子们放了。
这个小姑娘就是孟团长的女儿孟玲。这是我现在才对上号。我当记者以前,我无心无肺,似乎从没把我上高中后突然出现的同学孟玲,与青海民大那个孟团长的女儿,那个小妹妹毛美拉被“羁押事件”中后来出现的孟团长的女儿,做过等号。
那事儿,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那是拍马屁的那些警卫们干的,而是孟团长指挥干的,还是其妇人与女儿干的。我现在回望那事儿,仍是谁“羁押小妹妹们”我不知道,孟玲一定也是知道的。但是,是孟玲说把那些“羁押”孩子们全部放了。
前面说了,我考高中,成绩年级前几,可是因为我不听爸爸的话,傻乎乎地以为组织会相信在大巴山老家二伯被冤枉,在填写升高中表格时,在“亲戚有无重大历史问题”一栏填写了民大与附中都无人知道的“我二伯伯被枪毙”这件事,结果我升高中没升上。我只好插班红一师高二。可是我上高二没几月,民大附中(十六中)居然为了我把红一师(十五中)给告了:“红一师(十五中)非法录取了民大附中(十六中)已经录取的学生毛竹插”...............
红一师领导当然不愿为一个学生毛竹当被告。慌乱中让毛竹快快回民大附中报道。我只好回十六中报道。报道后我被分到了萧虎(化名)任班主任的甲班。萧虎同时是民大附中的教导主任。我更没有想到,萧虎老师把我要到他的班,不是为了爱护我,而为了更好地收拾我。而萧虎不是一个人,他的身后有校长冉大河,有原来的班主任与好多位任课老师。我没有想到,这以前,小小的我需要对付的是打我的“民间力量”;这以后,小小的我需要对付的是整我的“官方力量”。那是多么强大的“官方力量”,那时整个就是一个少女的天,天要压垮谁,谁能不垮?于是我加快了去宣传队的脚步。我知道,学校那些人再整我,可是不能阻止我去学校宣传队——他们不是为了学校荣誉把我弄回来的吗?我知道,在这个学校,除了有欣赏我的苏老师,更有宣传队喜欢我的老师集中在那里。宣传的丁桂珍老师、李立荣老师、郭老师都喜欢我呀,我总算有一个心灵寄托的地方。我恐怖了我可以疯狂跳舞。我惊惧了我可以投入音乐。宣传队,听说又要减人,可千万别把我减了呀!!!
高中甲的同学中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孟玲。我之所以用了一个“突然出现”。是因为只要是青海民大的子弟,我们多是从小学、初中都是校友,我们都熟悉。而孟玲我却没有见过——我忽略“小妹妹被羁押事件”中孟玲出现过。我更没有见把她与小妹妹们被羁押事件中的那个孟团长的姑娘联系到一起。这事儿不奇怪,我好像有一种记忆不愉快事情的功能。所以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大段的空白。有些空白随着时间与挖掘可慢慢恢复,有些空白永远是空白。
就算是我今天记起来了,我记得也是,小妹妹们被“羁押”七个多小时后,是孟玲走过来说:钥匙找到了!把小孩子们放了吧!
我和孟玲就坐前后桌。因为家都在青海民大,我们经常上学放学一起结伴儿走。我和孟玲都在附中学校宣传队,我们经常一起排练一起学唱歌。突击排练时,我们住一宿舍。排练完毕,我们一起回家。这让我们接触更多。
而前面文章说了,我被附中以打官司的方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