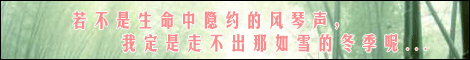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竹子申明:草稿正起,互动写作,欢迎参与,谢绝转载,转载必究!!!)
《胡杨林是怎么来的?》
——从新疆库尔勒上沙漠公路,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漠公路,向民丰方向行驶,行驶到n公里处,是塔里河大桥,沙漠公路两边可见一大片胡杨林。很多人奇怪,干涸的大沙漠中怎么会出现一片胡杨林?就算是有一条河塔里木河,也当是大沙漠中出现一条沿着河的胡杨树林带,怎么会在大沙漠中平白出现一大片胡杨树林呢?
知道吗?
这沙漠叫塔克拉玛干
这条河叫塔里木河
这树叫胡杨树。
这胡杨是长在塔里木河的两边的
可是塔里木河不听话
在沙漠中到处乱窜
不仅把树甩了
甚至把好不容易修的桥给甩了。
常常地人们看到
河在一边蜿蜒曲折
桥在一边寂寞冷落。
塔克拉玛干是沙海
管不住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姓野
大名叫野任性
小名叫野调皮
浑名叫野随意
按理儿
塔里木河跑了
胡杨木只能放弃跟踪?
可是不!胡杨木拗着呢
塔里木河窜到哪里
胡杨树就跟着长在哪里
塔里木河窜来窜去
像一个旷原野美
胡杨树追来追去
像一个痴情水种
胡杨木今天沿这条塔里木河故道曲折
胡杨木明天沿那条塔里木河故道蜿蜒
胡杨木清晨在塔里木弃道上呼唤
胡杨木傍晚在塔里木新道上冒出绿芽
不屈不挠
胡杨树跟来跟去
死缠乱打
总是要站在塔里木河边
为心爱的河遮风挡沙
总是要站在塔里木河边
怕痴爱的河再次跑掉
就这样追来追去
就这样窜来窜去
就这样你甩我跟
就这样你跑我粘
塔里木河在大沙漠中游荡
胡杨木跟着在大沙漠中游荡
胡杨终于成林
在塔克拉干沙漠中成林
这片胡杨林就是这样来的
《胡杨林是怎么来的》之二
她的名字叫塔克拉玛干
她想征服自己
包括那条名叫塔里木的河
为了让河不乱跑
她在河岸种了胡杨树
为了让河可跨越
她在河上修了桥
为了让河有责任感
她让桥上车来人往
可是她仍管不住她
因为她的内里没有岩石只有流沙
她是一堆飘逸的思绪
塔里河不听话
调皮顽皮狂野不羁
可是她仍管不住她
因为她的内里没有硬物只有曲线
她是一堆婀娜的曲线
塔里河不听话
调皮顽皮狂野不羁
今天把这行树抛弃
明天把这坐桥遗忘
早晨把这叮咛吹走
晚上把那嘱咐失落
她的激情神出鬼没
她的身影忽隐忽现
她的背影袅丽多姿
她的流向扑朔迷离
她拿她没有办法
她是本我
本我是她
唯有胡杨树不肯舍弃
跟着她声东击西
跟着她游击战术
跟着她浪迹天涯
跟着她山盟海誓
于是
那本来是对睫幽怨的胡杨木
变得行踪不定
变得影踪无踪
于是
那本来是两轨蜿蜒的胡杨木
变得多处留迹
变得风流倜傥
于是
沙漠中终出出现了奇迹
出现了一片胡杨林
《同一棵胡杨树上长着四种树叶》
我新奇的发现,
一棵胡杨叶上
居然有四种不同的树叶子
下面一圈老枝上是杨树叶子
中间一圈次老枝上是白果树叶子
上面一图次次老枝上是枫树叶子
最上面一圈嫩枝上是柳叶叶子
同一棵树上
杨树叶子圆润泛光笑脸重重
白果树叶子翩跹起舞神采飞扬
枫树叶子婆婆娑娑多彩多姿
柳树叶子腊光如镜妩媚晶莹
《我,可是塔克拉玛干一棵千年胡杨?》
就好像我站立着
名叫胡杨
一棵树上却有四种不同的叶子
杨树叶子
白果树叶子
枫树叶子
柳树叶子
就恍惚
为了战胜风沙
我可以变来变去
就仿佛
为了战胜自己
我可以一截一个样
《胡杨的传奇》
我第一次走进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看到大片的胡杨木
有活的 有死的
有干的 有湿的
有站的 有倒的
有死了千年发新芽的
有活着千年举腐干的
有地狱张口呼唤妖怪的
有天宫高悬吸引仙灵的
有成仙女的,有成魔鬼的
有成将士的,有成懦夫的
有成狮子下山的,有成老虎上山的
有成鳄鱼的,有成恐龙的
《废桥》
你曾征服过塔里木河
横跨她的顽皮
镇住她的任性
收住她的情思
钉住她的躯体
缚住她的野性
为了收服她
你曾付出几许
那几只桥足探入沙漠二十米
因为那像流动的海底
那几根桥桩里每一次都浇筑四十根钢筋
那几根桥桩外砌青砖块块是兵团人精心烧制
那桥栏是兵团人从天山运来的长石
个个都雕有降龙伏虎的咒语
那桥面是农一师人从天山运来的方料
块块都融进镇山定地的魔语
可是桥没有想到
塔里木河居然跑了
可是桥没有想到
塔里木河居然这么就跑了
唯留相思打弯
唯留情怨伏地
唯留桥自己
孤苦伶仃
像一个遗弃远古的恐龙
桥想跟着跑
可是它被那咒语定住了
跑不动
只有低头
默默地感知
飘来飘去的
它的爱人
它的塔里木河
桥想跟着狂
可是它被魔语钉住了
跑不动
只有低头
悄悄地感知
踪来踪去的
它的爱人
它的塔里木河
《桥在一边》
桥在一边
河在一边
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才有的风景
《桥在思考》
河在水里屏息敛气
只想着再次逃跑
桥在岸上凝重思考
像诸葛亮足智多谋
桥与河居然无关
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深的阴谋
桥在思考》
河在水里屏息敛气
谋划着下次出逃的方式
桥在岸上凝重思考
思考着下次拦截的方位
桥与河终身大战
桥与河终身棋局
都说这才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深的智谋
《塔可拉玛干才有的独特风景》
河在野地潇洒不羁
桥在远远的岸边抵头休息
河不在桥上
桥不在河上
桥与河两无干系
桥离河足有三百米
桥只如一个被激情废弃的鳄鱼
站在河的一边
在那里沉重地喘气
桥只如一个被任性遗弃的恐龙
卧在河的一边
无奈中低下沉重的头
《桥的叹息》
(那一次,我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农一师出来,塔里木河过不去,遭遇”世纪大堵车“。我蹲在地上,往后看,是几千辆装满”高耸入云棉花“的巨型东风牌大卡车。被堵的大卡车在塔克拉玛大沙漠中蜿蜒远去,像一条巨龙,尾巴恍惚融进了朝阳中。原来那正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棉花大丰收的季节。原来大丰收的棉花正等待运向全国各地。谁也没有想到,巨大的车队居然看起来被这么小的塔里河——可能只是塔里木河的一个支流堵住。
我往前看,只见一座废桥在离河很边的一边”宏伟地喘气“,无奈地注视着”临时渡口“。临时渡口只有木栈道,只有几小船。这何时才能渡装满”高耸入云棉花“的几千辆巨型东风牌大卡车?真是恨不很让卡车直接冲河过去。压河过去。那河看起来并不宽。可是细看那沙漠中的野河,可不简单,更不一般,急流喘息的声音惊天动地,当浪钻入沙洞中再冲出来带出魔鬼地狱般的轰鸣。是的,整个大沙漠都在颤动。那是一种吞没一切的阵式呢。那河一定深不可测呢。别看它看起来不宽,却难住了这几千辆大卡车。
那一次,送我的出来的人说:你快快拍照吧,我虽然不是记者,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普利策新闻奖,今天就是你获得普利新闻奖照片诞生的时刻。我答到:我怎么不想拍,你不是看见我刚才上了沙丘,可是我回来了。为什么呢?原来,我那一次虽然拿着上好的相机——那是中国石油记协的摄影家听说我要来沙漠特意让我带上的最好的相机,可是电池的电却已经被我耗尽了。我只能望好的”利新闻奖照片“而叹息。
可是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却从此定格在我的和生命中,让我一次一次回望,心里充满了震憾。)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受伤的恐龙
看着塔里木河奔腾咆哮
钻进沙漠的洞里
又摧毁地狱连沙带泥冲泄出来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失败的鳄鱼
看着几千辆东风卡车
拉着高耸入云的棉花
等待摆渡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遭受重创伤的狮子
看激流上的木排承不住大吨位的东风卡车
看那木栈那么单薄
看那渡船那么瘦弱
看那东风卡车被激流冲走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濒死的老虎
看几千个巨垛一般车队
堵到天边
堵到夕阳里
已经堵了多少白天黑夜
怒气冲天
血色黄昏
《桥的叹息》之二
桥在河的一边
像一个护佛受重伤的阿卡
匍匐在地
鲜血流淌
无法再上前
只能看着塔里木河像魔军奔腾咆哮
钻进沙漠的洞里
又摧毁地狱连沙带泥冲泄出来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护佛受重伤的阿卡
看着他护的几千座大佛
像几千辆东风卡车
拉着高耸入云的棉花
带着高耸入云的微笑
等待摆渡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护佛受重伤的阿卡
看着他护的几千座大佛
一个一个上了激流上小小的木排
看几渡船承不住像承受不住大吨位的东风卡车
看那木栈那么单薄
看那渡船那么瘦弱
看那大佛被激流冲走
桥在河的一边叹息
像一个护佛受重伤的阿卡
看几千个座大佛
像巨垛一般车队
堵到天边
堵到太阳里
已经堵了多少个白天
《塔里木河》之二
我回眸
我再看了一眼塔里木河大桥
我再看了一眼塔里木河大桥下的塔里木河
塔里河真的正从桥下流过吗
我为什么看不到一丝儿涟漪
我为什么觅不到一丝儿波澜
我为什么寻不到一丝儿波动
我为什么找不见一丝儿流动
塔里木河真是太静了
静得看不到一丝儿动静
如同一个一万年前的铜镜
倒映出旧石器时的风景
收敛着新石器时的风声
吸纳着远古的嘶喊声
珍藏着近古的出鞘声
深不可测
《塔里木的烤羊肉串儿》
这里离塔里木河大桥不远
新疆当地人站着一排
长长的烤箱内木碳火红红
他们在用胡杨木根雕给路人烤羊肉串儿
新疆人说:吃嘛!吃嘛!
烤羊肉串儿
胡杨木烤出的羊肉串儿
天下最好吃的羊肉串儿
中国最环保的羊肉串儿
新疆最喷香的羊肉串儿
真真的三千年古木烤出的羊肉串儿
除了在塔克拉玛干
其它地方吃不到
不吃的话
你会后悔三千年
不吃的话
再过多少年
这一片胡杨林的吗会不见了
原来吗一大片
原始森林的个是了
已经吗越来越少了
没有办法
我们要生存
若不是
早就没有了
你们还能吃上
幸运的个很吗
“这胡杨站着不死一千年”
“这胡杨死了不倒一千年”
“这胡杨倒了不腐一千年”
三千年的香味儿
其它地方哪里有
不吃的话
你会后悔三千年
《煮熟千年的牛肉》
那片倒下的胡杨树
倒下的姿态各不相同
我眼前一那棵倒下胡杨树
让我想起壮士山倒
让我想起勇士后倾
让我想起力士驾崩
让我想起
项羽三万兵对刘邦六十万
让我想起
垓下之战
十万战五十万
蚂蚁成字
四面楚歌
让我想起
项羽自尽
身子仍倔强
骨子仍壁立
力拔山兮气盖世
让我想起
虞姬先自刎
尸体仍优美
有遁音回荡
虞兮虞兮奈若何
我细看“项羽的身子”
木质丝丝缕缕
像煮熟的牛肉一般
想动一下
却是化石一般坚硬
《碎钉阵》
那边
一棵胡杨木
不幸被谁砍去身子
那余下的木墩子
那剩下的根墩子
居然如一个“碎钉阵”
那样展开
如万剑眦目
如万弹勃发
有些儿恐怖
恍惚谁触一下“碎钉阵”
就是万剑齐射
就是万弹齐发
射向路过的商人驼队
仿佛谁动一下“碎钉阵”
就是万钉射发
就有万钉勃动
刺向隐性的魔鬼天兵
小心翼翼绕那“碎钉阵”
那可能同样硬如化石的木墩子
小心翼翼绕那“碎钉阵”
就如不想仙界神界魔界鬼界
死太多“人”
《地狱中爬出的恐龙》
你不就是一个根雕吗
怎么像刚从地狱中爬出
干嘛那样张牙舞爪
干嘛那样呲牙咧嘴
干嘛那样鬼鬼祟祟
干嘛那閪恐怖惊惧
是想告诉我们
你见到的那个沙漠真相是多的肃人吗
《想起刘病》
这根雕
病态的匍匐
失落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汉武帝的孙子刘病
它像是我们人类的刘病
被风沙珍藏在这里
它的回想风沙弥漫
它的回忆风沙走石
刘据在大沙漠背景上拉开
刘病你不是汉武帝的孙子
刘病你不是刘据的儿子
你怎么跑到这里
你父亲刘据不是不幸被定为太子
你的奶奶卫子夫是卫青将军的姐姐
你的爷爷的姐姐嫁给了卫青将军
你的父亲不是太子刘据吗
这么显赫的身世
你怎么跑到大沙漠孤独流落在这里
你的父亲刘据不是不喜欢爷爷
召将讨论战事吗
你怎么跑到这大沙漠里寂寞流落在这里
难道巫蛊之乱真的与你有关
难道你真的让你的爷爷汉武帝与父亲刘据太子不幸兵戎相见
难道你真的让你的父亲刘据兵败之后选择自杀
让你的母亲卫子夫内乱之后选择自尽
不然为什么
风尘不肯言
冤枉不肯说
难道真相终于水落石后
那一阵乱刀
处决了瞎报情报传谣扩谣四种人
仍没有止痛你的失落
让你在这里生病
让你在这里忍病痛几千年
你不是被汉武帝从大狱捞出
你不是被称作汉宣帝
可是你为什么没返汉室皇族
不是说你被送到父母家里
远离权力争斗
你怎么一个人独自屈就在这里
思子宫在遥远的汉宫隐现
刘病
《根雕站着的样子》
还真是
许多根雕站着不倒一千年
就是不知道名字叫什么
其中一个
就是让我想起西域名将霍去病
一生威武的样子
《根雕站着的样子》之二
还真是
许多根雕站着不倒一千年
就是不知道名字叫什么
其中一个
就是让我想起称为西域名将卫青
霍去病也不过是他的外甥
想卫青与霍去病两代大司马
想卫青开河西酒泉是不是来到这里
想这海市蜃楼是不是再现其“大战匈奴”
一场一场又一场
我仿佛听见卫青在说话:
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也
《三句形容塔克拉玛干的“俗话”》
我刚到报社
社大头名叫王复印
王复印曾是大庆油田大头
曾管职工十几万
现管报社职工几百个
实管一百多万大脑
他告诉我们
遥远的新疆有一个沙漠叫塔克拉玛干
他告诉我们
塔克拉玛干中有一片胡杨木
太神奇了!
像一片外星人的遗地
他告诉我们
那片胡杨木
站着不死一千年
死了不倒一千年
倒了不腐一千年
后来
我亲自来
反复听新疆人说这三句话
再后来
我没有来
听中国人说起塔克拉玛干
反复听见这三句话
都说这几句话
仿佛塔克拉玛干已经不能再形容
这三句话
王复印先复印了谁的
已经无法考证
这三句话
谁先复印了王复印的
已经无法考证
反正说起塔克拉玛干
中国人都这三句话
谁被复印
谁在复印
谁被洗脑
谁能自拔
平心而论
这三句话
说得实在是好。
只是
第一个说时
实在是好
第二个人呢
第三个人呢
而我说这三句话时
是第几个人
这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相关的人
是不是都叫王复印
《那胡杨少女“根雕”》
这片胡杨木林
吸引了许多的摄影爱好者
来沙漠“抢救”
拍的照片
有一幅
一生难忘
深刻印象
拍摄的对像
是一棵胡杨“根雕”
风沙正是那个雕刻手
在夕阳下
那根雕成一个剪影
像极了一个少女的侧影
那少女
脸廓丝滑
线条柔美
鼻子高棱
长发飘逸
裙裾摇曳
在夕阳下
那真像一个少女
栩栩如生...............
少女在沉思?
少女在思念?
少女在憧憬?
少女在畅想?
少女正陶醉?
《根雕最后的样子》
根雕再丑陋
根雕再恐怖
根雕再阴森
如果请大漠风沙做雕刻手
雕出的最后作品
一定是一个少女
一个绝代芳华的少女
一个简单 明镜 天真的少女
一个真情 嫩稚 幼拙的少女
一个纯情 痴情 真情的少女
《根雕最后的样子》之一
根雕再丑陋
根雕再恐怖
根雕再阴森
根雕再老朽
如果请他雕刻自己的终极偶像
雕出的作品
一定是一个少女
绝代芳华还需像少女一般对他简单 明镜 天真
绝代优姬还需要像少女一般对他真情 嫩稚 幼拙
绝代名妓还需像少女一般对他纯情 痴情 真情
绝代娇虞还需像少女一般娇羞 青涩 痴情
《根雕最后的样子》
根雕被风沙雕刻后
最后的样子
一定是少女的样子
一定是让风沙可沿
最顺畅曲线掠过
最畅流弧线划过
最优美曲线掠过
最婀娜弧线划过
根雕被风沙雕刻后
最后的样子
一定是少女的样子
《最后的定格》
如果请风沙做雕刻手
那么在这大沙漠中
胡杨根雕最后的定格
一定是一位少女
一位长发可让流沙缓缓流过的少女
一位曲线可让长风漫漫滑过的少女
一位曲线能让岁月静静流过的少女
一位目光能让长河悄悄融化的少女
《最后的定格》之二
如果请风沙做雕刻手
那么在这大沙漠中
胡杨根雕最后的定格
一定是一位少女
一位可以流淌成线条的少女
一位长发飘逸可让流沙平滑流过的少女
一位曲线婀娜可让思绪平滑缥过的少女
一位思绪起伏能让时光平滑消逝的少女
一位目光缥缈能让长河平滑流去的少女
《最后的定格》之三
如果请风沙做雕刻手
那么在这大沙漠中
胡杨根雕最后的定格
一定是一位少女
一位是一位最光滑的少女
一位曲线流淌让目光掠过的少女
一位长发光滑可让流沙缓缓滑过的少女
一位皮肤光滑可让思绪缕缕滑落的少女
一位思绪光滑能让时光款款消逝的少女
一位目光光滑能让长河静静流去的少女
《沙漠中的蜥蜴》
你从来都是在人的脚下蹿来蹿去
可是今天
你走过来
居然比我高出半格
你甚至让我
举头凝望
像看一个让我敬仰的人
《沙漠中的蜥蜴》之二
你从来都是在我的草丛中蹿来蹿去
可是今天
你走过来
和我一样平起平坐
你甚至让我
庄重凝视
像看一个让我佩服的人
《沙漠中的蛇》
不就是到了沙漠
你怎么能这么走路
不就是到了沙漠
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不再是往前梭进
你不再是向前蜿蜒
你变成了身子上下曳动
你变成了不着地的曲线
你变成了飞翔着的曲线
你的步履怎么能呈现波浪状
你的身子怎么能呈现波浪状
你是看沙漠是波浪
你就成了波浪
你是看风儿变成波浪
你就成了波浪
你是看声音成了波浪
你就成了波浪
原来你是变成了沙漠的模样
原来你是变成了风儿的模样
原来你是变成了声音的模样
在大沙漠中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
《沙漠中的蛇》之二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所以变成了波的样子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
所以变成了浪的样子
你是不是悟到了什么
所以变成沙漠的样子
《沙漠中的蛇》之三
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变成了这样
你像一道水波在光中荡漾
你像一道光波在水中飘动
你像一段岁月在风中沉浮
你像一段记忆在空中迷茫
《着银色宇宙员服装的蚂蚁》
小小蚂蚁
你不就是在沙漠中吗
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就是在沙漠中吗
你不就是出洞觅食吗
干吗要装上银色的宇宙员服
干吗要银光闪闪
干吗要寒光铮铮
干吗要收腹挺胸
干吗要精神矍铄
干吗要出门像打仗
干吗要回洞像赴死
干吗弄得那么悲壮
不就是地面温度摄氏70多
不就是生物种类已剩不多
你们干吗这般全副武装
《着银色宇宙员服装的蚂蚁》之二
小小蚂蚁
在地面温度摄氏70度的大沙漠
难道你不是热而是冷吗?
难道热到极致你不是热而是冷吗
难道极热你不冒热汗而是发寒光吗
为什么身子变成森森盔甲
为什么样子变得精骨嶙峋
为什么行动变得铮铮铁骨
为什么形状变的寒光凛冽
难道热到极致你不是热而是冷吗
难道极热你不冒热汗而是发寒光吗
《塔克拉玛干是流动性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性大沙漠。也就是说,那些沙丘的形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幻莫测的。如果从空中俯瞰拍摄,然后
快放,那么,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像真正的大海一样,白浪滔天,波澜起伏。
当然,我说还有海涛声隐隐约约传来。你信吗?
这可是真的!
为什么呢?原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挖下一米就是海水,但是不能喝。只能望水兴叹。
这也是,为什么探险者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迷路,且总是转不出来,因为不论你留下多少路标多少标记,它们都会失踪在流动的沙丘中。
这也是,为什么探险者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迷路,总听到大海的海潮声,却找不到大海。不论你走了多远,不论你看到了多少次的海市蜃楼,也找不到真正的海。
这也是,为什么探险者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挖到了水,可是却活活渴死了。
因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几乎没有淡水,多少探险者与经商者有进无出,所以被当地人称作“死亡之海”。
《我曾睡在“死亡之海”的底部》
现在的人们一定不知道,现在已经有两条沙漠公路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与腹地穿过。而沙漠公路可直达我们中国石油的塔中四油田。
沙漠公路可从库尔勒到塔中四到民丰。
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心里”,长年住着我的石油人。当然,当年我野美毛竹也野到那里,也在那里住过。那是一种睡在波涛汹涌大海底的感觉,真的很稀奇,真的很独特。
《管二公司库善线项目经理讲的故事》
我记得当年我采访管二公司,公司经理给我讲的几个故事
那一年,石油管道二公司的队伍进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可是队伍进去了修库善线的管道却没有运到。等管时间居然是漫漫长长的一个月。
这一个月对石油职工可是比一年甚至十年不长呀!职工们不敢乱跑怕失踪,不敢乱进怕迷失。可是天天呆在工棚子里,急得要疯了。怎么办
呢?
项目经理说,我天天无事可干,就拿望眼镜侦察,转圈圈侦察。我发现我们的职工天天早出晚归。他们不敢走远,就在能看到营地的沙山转
圈圈,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早上出去晚归。转了整整一个多月。
《失踪的他》
他是管二公司的职工
失踪地点是火烧山
你喝了点酒出门游荡
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还不回到你的家乡
你是还在火烧山寻觅已经转移的队伍
你是沿蛛丝蛇迹追下一个施工点塔克拉玛干腹地某点
你是顺风踪暴遗迹找到鄯善未站
你是半路被彭加木拐走
告诉我们这么多年你到底在哪里游荡
告诉我们这些日子你到底在哪里流浪
难道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玩够
让我们将你与新疆一起回想
一起混响
一起幻想
一起畅想
你喝了点酒出门游荡
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还不回到你的家乡
《守口如瓶》
这是管二职工悄悄告诉我的秘密
二十多年我守口如瓶
沙漠职工规定不能喝酒
违纪“军法论处”
可是干管道管子没到
漫漫岁月怎么能没有酒
于是几瓶酒被悄悄带入
于是几瓶酒被悄悄埋入沙丘
总也是几个人转来转去才转到这里
掏出来才有几口对饮
他们没有想到
塔克拉玛干是流动大沙漠
有一天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埋入的酒
后来他们走遍天涯
每到有酒下肚他们就会面西南
想那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烟中
神秘隐现的几瓶酒
几瓶他们的酒
后来他们走遍天涯
每到有酒下肚他们就会面西南
想那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波涛中
神秘旋转的几瓶酒
几瓶他们的酒
那是他们几个人
二十多年的秘密
他们知道
有人为他们守口如瓶
《两只小丽鸟儿》
的吐鲁番管道三公司的工地,我毛竹发现了两只小丽鸟儿。这两只小丽鸟儿,长长的嘴巴,是红色的;长长的尾巴,是白色的。腹部长长的一道是翠绿色的,背上却是赤澄黄青蓝紫,五彩缤纷。
真是太漂亮了。我忽然好奇:这里像月球一般荒凉,没有水,没有草,没有树,没有生命,只有碎石,这两只小丽鸟我在哪里生存呢?我开始观察。
几次我去上厕所,都有鸟儿腾飞,细看,原来正是那两只小丽鸟儿。
原来这小丽鸟儿就生活在管道人临时搭建的厕所中
《担心》
从新疆库尔靳到喀什的路上
我在望着掠过的院子
干打叠的院子
我在为它们深深担忧
因为上一次来回
因为上一次进出
好些掠过的院子
干打叠的院子
我去时有人住着
分明是热热闹闹的
分明是灯红酒绿的
回来却成废墟了
出来却成荒园了
杳无人迹
杳无声迹
就连追过我的两只大土鸡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相思》
这么多年
好些事儿都忘了
那些土院子
那个土庄廓
那些蹿动的人影
唯记着两只大土鸡
白色的
红色的鸡冠
高骄的鸡胸
拔长的双腿
足有半人高
追着我
让我不敢轻易进院
让我不敢草率出门
《路边,上百辆事故车》
那年在新疆
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已有公路
那公路看起来平平的
那公路看起来展展的
那公路看起来长长的
那公路两边建筑物很少
那公路两边不是荒原就是沙漠
那公路两边不是沙漠就是荒原
那公路叫国道看起来直直的
那公路来回两条看起来互不侵犯
那公路看起来像是天下
最好开车的路
就算是打瞌睡冲到路边
不就是撞进野地跑些毛路拱些泥沙?
于是来回车道上的车
都开得疯快
多快活呀
三千公里尘与土
多痛快呀
八万公里云与月
当两辆车平稳错车
却常常撞到一起
原来
那公路年久失修
原来
那公路早已经是藏匿坑洼
那公路早已经是埋进玄机
那公路早已经是跌入暗算
就如他与她
各自走着各自的路
相向而行
错车时
端庄平稳
目光向前
却不知道怎么搞的
撞在一起
那些年
从喀什到乌鲁木齐有多少公里
一路上躺着上百辆的事故车
那些年
路边的建筑物不过
放眼望去
一路边的事故事
《不死草》
谁说不死草她不死
其实她已经死了
死前
她只是胳膊大腿抱在一起
抱着一个梦
看起来
如一个抱成团的骷髅
从哪个方向看
都是黑洞眼睛
谁说不死草她不死
其实她已经死了
唯留一个梦还在挣扎
就如干枯的胳膊大腿
抱了数个遗腹种子
谁说不死草她不死
她已经死去百年
只能任骆驼把她踢来踢去
只能任沙狐把她抛来抛去
谁说不死草她不死
她已经干化百年
只能任小蜥蜴偶尔藏身
只能任小蜘蛛偶尔躲阴
忽然的风来了
忽然风沙来了
把死了的她吹来吹去
忽然沙暴来了
把干了的她滚来滚去
在沙丘上她被碰得叮叮咚咚
在沙壑上她被撞得听听统统
终于遇到水了
不死草她停下来了
她死了干枝滋润后打开了
就好像是死前抱紧的胳膊大腿
终于展打开了
渴望的雨终于驾倒
打落她手里捧着的种子
脚里夹着的种子
种子入土几小时就破土而出
几周就开花结果
不死草下一代她又被晒死了
不死草她死前又抱着自己的胳膊大腿
她与所有的植物一样
只是抱着种子
等待着种子再次发芽
谁说不死草她不死
仅是她的种子不是年年发芽
而是期盼好多年
才发一次芽
且要等待机遇
《不死草》之二
谁说不死草不死
它已经死了一百年
奇迹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而是她的遗腹子身上
也如母亲已经死了一百年
腹中的婴儿居然还活了
且不是一个
而是多个
《不死草》之三
都说是复活的奇迹
其实根根就没有看清
“草骷髅球”终于被风吹到有水的地方
水终于泡到'草骷髅球'“肢杆”上
“草骷髅球”从来没有复活
那就是死后不甘心的模样
只是“草骷髅球”遇水
终于打开“死爪”
雨水趁机可把“遗腹子”从“死爪”“死胎盘”中夺出
雨水趁机可把“遗腹子”种进地里
雨水终于可风周内护它发芽开花结果怀孕
“遗腹子”又死了
成了新的“草骷髅球”
“遗腹子”的“遗腹子”
又开始了“草骷髅球”的飘零
“遗腹子”的“遗腹子”
又开始了“草骷髅球”的游荡
《不死草》之四
不知道母亲与孩子之间年龄的断档
怎么计算
更头疼的是
没有规律可寻
这一代与下一代
相隔不是一年而x年
这么多的空档
夹在这上一代与这一代
这一代与下一代
或是一年或是百年
或是五十年或是几百年
就是这些死的年
会不会扰乱公历或是农历
让人类的世界纪年
乱得不成个样
《不死草》之五
谁说不死草不死
它早就死了一千年
只是怀里的种子没死
就如出土的
楼兰美女
人们忽然发现她千年前怀孕的胎儿还活着
《不死草》之六
她已经死了
活着的是她的胎儿
你偏说她没死
这是偷换概念
就如人类
她死了
女儿还活着
你偏说她还活着
这是偷换概念
要知道
她与她女儿
她与她孙女
她与她重孙女
就算是长得像
也不是一个
就如她不可替代
《接车经历》
大一次下去采访,早上在大河沿火车站下了火车,管三公司的人说派车来接我。等了几个小时,为什么还不来接我?我打电话,说是大风过不来。一直等到下五点多,公牛车才到。我心中有些儿不高兴。不想接就不接,骗谁呀!一个大风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大风能耽误十来个小时?害得我一个人在火车站逗留这么久。
我上了车往三公地基地走,我才发现我错怪了接车的三个人。他们如果硬接不仅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而且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一路上全是碎玻璃,那是多少辆车的玻璃呀!那碎白玻璃如果数不清的珍珠玛瑙碎玉水钻金镯银簪,在路上,在路两边闪烁,着实震撼了我。
路边躺着好多辆车,那都是被我吹倒的。想想,司机一定是受了伤,这些车才没有人管。
我这才知道这片我区的厉害。
我这才知道,这一带,长长的火车都被吹翻过。
我这才知道,这一带,满载的货车常常被风吹倒。
《领教大风》之一
大风你想干什么
您想把车窗玻璃
全部变成洒落一地的珍珠玛瑙
大风你想干什么
你想把车窗玻璃
都变成铺向天宇的碎玉水钻
大风你想干什么
你想把车窗玻璃
都变成能向太阳的金镯银簪
你想替我们擦车吗
你干嘛用那么大的劲儿
你没看到侧柒都被你擦没了
你没有看到车灯都被你擦毛了
你没有看到轮胎都被你擦花了
你帮助擦车就擦吧
用那么大劲干什么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速度那快做什么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干嘛不用水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干嘛一个劲干擦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干嘛用的抹布这么大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那么喘为何不歇息一下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一个人就够了干嘛动用千军万马
你帮助擦就擦吧
你动用千军万马擦一车几分钟当就完了
为什么擦得昏天黑地
你还不叫千军万马停下
你告诉我
你要把车擦没吗
你要把我们擦没吗
《领教大风》之三
那一次,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坐车到库尔勒,从库尔勒坐火车卧铺到吐鲁番。先半夜,突然醒了,感觉不对,感觉风,像数条海蛇钻进了火车,发出滋滋的叫声,且带着深海的腥味儿。
仿佛那海蛇钻进了我的骨缝中,摇曳,向远方,向远远方
我似乎到那无限摇曳出云的海蛇还是海浪,感觉它们与深圳珠海海南岛以外的的海沟或是深海连在一起的。
再细听,那整个火车都像在深深的大海中,那远的近的大海波涛声也是那么真切。可有一种真切的感觉,那车窗外的大海波涛声与车窗内的大海波涛声是一体的,仿佛整个车已经与“大海浑然一体”。仿佛火车的车窗与绿皮车身已经完全不存在。我已经完全地置身在大海中。
那种感觉真是太怪异了。
我定眼再看,似乎不仅车窗外的夜色仿佛变成了钢蓝色的海水,而且整个卧铺车箱都隐现在钢蓝色的海水中。
我再也睡不着,这感觉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真是太奇特了。莫不是我在梦中,我闯进了真正大海的海底?我自己掐掐我自己有痛感。我不在梦中呀。
我禁不住问列车员:这是我吗?列车员说:这是风!这里是大河沿风口。
《大河沿风口》
大河沿风口
原来你有一种功能
一种消失列车车皮与车窗的功能
你分明让列车车皮与车窗都不存在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深处的波涛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的浪与我车箱的浪浑然一体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中呼吸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与另一只海豚遥相呼应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一群鲸鱼从我头顶掠过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一群鲨鱼在我侧边游过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有一群浮萍在上空开发烟花一样
我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有一群电鳗在黑暗中扑朔发光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的一个小小的波动都荡漾在我的心里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的一个小小的异动都传递在我的耳里
《大河沿风口》之二
大河沿风口
原来你有一种功能
一种穿透列车车皮与车窗的功能
你分明让列车车皮与车窗都不存在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深处的波涛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的浪与我车箱的浪浑然一体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中呼吸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与另一只海豚遥相呼应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一群鲸鱼从我头顶掠过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一群鲨鱼在我侧边游过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有一群浮萍在上空开发烟花一样
我分明让我感觉到我在深海有一群电鳗在黑暗中扑朔发光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的一个小小的波动都荡漾在我的心里
你分明让我感觉到大海的一个小小的异动都传递在我的耳里
《大河沿风口》之三
大河沿风口
原来你有一种功能
一种穿透列车车皮与车窗与我的功能
你分明让列车车皮与车窗与我都不存在
我真是已经不存在
我分明感觉到我变成了大风
我分明感觉到我游进大海进深
我分明感觉到我就是大海深处的波涛
我分明感觉到大海中的呼啸是我的呼啸
我分明感觉到洋地的呼吸是我的呼吸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海豚与一只海豚擦肩而过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鲸鱼与一群鲸鱼比翼跳跃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鲨鱼和一群鲨鱼交换口语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海象同一群海象忽明忽暗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水母在一群水母忽隐忽现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电鳗在一群电鳗扑朔迷离
我分明感觉到我是海蛇同一群海蛇神秘发光
我分明感觉到大海的一个小小的波动都荡漾在我的心里
我分明感觉到大海的一个小小的气泡都源自在我的肺里
《大河沿风口》之四
我忽然感觉
我变成了绿毛龟
深海中的绿毛龟
绿毛长长的随大海波起
我忽然感觉
我变成了绿毛龟
深海中的绿毛龟
绿毛长长的随大海宽广
我忽然感觉
我变成了绿毛龟
深海中的绿毛龟
绿毛长长的随大海宽广
我忽然感觉
我变成了绿毛龟
深海中的绿毛龟
绿毛长长的随大海发光
我忽然感觉
我变成了绿毛龟
深海中的绿毛龟
绿毛沉浮 潮起潮落
《大河沿风口》之五
蓦然醒了
感觉不一样
仿佛寒冷不在车窗外
而是钻进来
如蛇一般种在我的骨缝中
然后曳动
让我感觉十万八千里外的大海
还有那中的冷光
倏然醒了
感觉不一样
仿佛风声不在车窗外
而是溜进来
如鳗一般种进我的骨髓中
然后摇曳
让我感觉十万八千里那么长的大风
还有那风中隐约的地球
《屎克朗》
大沙漠边缘最好观察你
你得到粪球
你就倒立了起来
推你的大梦想
心中就想着爱人
就想着拿它去献礼
只有了方向
没有了路
虽然你几次滚下深渊
虽然你几次掉下悬崖
你无悔无怨
你几扑几起
你得到粪球
你就倒立了起来
推你的大梦想
心中就想着爱人
就想着拿它去献礼
只有了方向
没有了路
《塔克拉玛干》
你更似凝固的大海
你把大浪的浪涛凝固在沙丘中
你把海啸的风暴收纳在沙壑里
你把鲨鱼的欢乐吸藏在每一粒沙子里
你把海豚的呼唤珍藏在每一道沙痕中
《塔克拉玛干》之二
每到深夜
你就变成了大海
波涛汹涌
白浪滔天
海风呼啸
飓浪澎湃
你就变成了大海
辗转反侧
心里呼唤着一个名字
每当凌晨
你就是你了
一个纯粹的女人
一个水做的女人
线条在风尘中隐现
曲线在风沙中流连
每到凌晨
你就变成了大海
辗转反侧
心里呼唤着一个名字
《最执拗的是什么》
最执拗的看起来好像是河
最执拗的看起来好像是树
最执拗的看起来好像是野兽
最执拗的看起来好像是人
其实我们都错了
最执拗的其实是沙丘
你看它
不论你们怎么攀爬它
滑沙时分明已经把沙锋带下
第二天它仍悄悄恢复原状
那高度你量一下分毫不差
你看它
不论大风怎么削减它
不论驼队怎么扭曲它
第几天它一定要恢复原来的弧度
那曲度你测五分廛不差
你看它
不论酷暑怎么折磨它
不论海市怎么毁灭它
第几年它一定要补好自己的伤口
你看它
不论岁月如何破坏它的曲线
第几世它一定弯成来世的模样
你看它
不论时光如何干扰它的弧度
第几春秋它一定要精确到初出的形状
它静悄悄地舔舐在旷无人谜的“海底”
它静悄悄地修复在干渴残酷的“绝地”
其实我们都错了
最执拗的其实是沙丘
《最硬的是什么》
最硬的好像不是银丝
最硬的好像不是金丝
最硬的好像不是银丝
最硬的好像不是钢丝
而是沙丘上的弧线
你看看
好像无论什么力量
都不能改变它一点点
准确到微毫米
精确到微毫米
纵有几千万年
丝毫不乱
《不断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
似乎什么都断了
唯有沙丘的曲线
没有断
它如蜥蜴的断尾
就算是断了
也能自己续尾
它如蚯蚓的身子
就算是断了
断成多节
也能自己续接
《不变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
似乎什么都变了
城市变了
乡村变了
田野变了
沼泽变了
唯有沙漠不肯变
默默地
一次一次又一次
恢复原来的样子
《在大沙漠腹地静卧》
野母狼误闯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由公野狼独有的营地
野母狼躺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心
野母狼躺在流动大沙漠“死亡之海”之心
聆听成百上千头野公狼在发情中翻滚
恐怖的夜由带血丝的眼睛构成
寂静的夜由存杀机的欲望构成
野公狼已经被围困营地三个月
母野狼知道一年有几个三个月
母野狼的体内也是埋伏千军万马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似乎需要母野狼一路“撒尿”
标注领地
声明地盘
不然如何安定
不然如何安宁
不然如何沉静
不然如何安静
烙饼在塔克拉玛干之死亡之海的心上
母野狼知道自己是唯一一头母兽
母野狼知道自己
必须克制
母野狼知道自己
必须必须克制
母野狼知道
稍有动作
公野狼的队伍就会乱成真的千军万马
母野狼知道自己
必须克制
母野狼知道
稍有动作
公野狼的队伍就会乱成真的刀光血影
恐怖在纵容
惊惧在操动
绝望在谋划
在被毁灭之前
前毁灭整整一个大营
想在野地撒野
想在野心狂奔
想俘虏饮血
想茹毛吮血
想饥饮公狼血
想渴食公狼肉
想和千军万马混战
想和千军万马血拼
野母狼必须克制
在野地之心
母野狼知道
恪守的战场转移来转移去
发生在塔克玛干大沙漠“死亡之海”的心上的恪守
最是难忘
辗转翻侧的烙饼
在“死亡之海”的“心炉”上
这好像很是悲壮
《大沙漠腹地,你听到了什么》
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底
静卧
她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针尖在画布上移动
像有个十百千万位工笔画家
同时画画
《大沙漠腹地,你听到了什么》之二
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底
静卧
她听到了什么
她听到笔尖在白纸在来回擦动
像进到了美术系的教室
像有个十百千万学生
同时画画
《大沙漠中的路灯》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没有电却有路灯
那是神奇的路灯
那是不用电的路灯
那是光芒万丈的路灯
那是活力扫射的路灯
当公牛越野车没有开上沙漠公路之前
沙漠公路一片黑暗
路灯是有但没有亮光
奇迹就发生在公牛越野经过的一刹那
车灯照在路灯上
路灯哗哗全光
光芒突破长夜
光荒射破苍穹
原来那并不是路灯而是反光版
原来汽车的反光也可以这样
左一拐弯
一排射向沙漠腹地左翼
右一拐弯
一排射向沙漠腹地右翼
如可穿透一切魔鬼的一排刺刀
如可穿越一切妖怪的一排利剑
《草方格》
谁同意你的
在她的袅娜的身体上打上方格
谁批准你的
在她的婀娜的身体上盖那多印章
你想固定她的身体吗
你想凝固她的思绪吗
你错了
你知道她是大海的一部分
你知道她是宇宙的一部分
她可能会动不了
但是她可呼唤
她可能会动不了
但是她会呼啸
你可知道
她一呼唤全世界的海水就来了
你可知道
她一呼唤全宇宙的暴风沙都来了
你想让她不动
你想让她不能翻身
你可知道
她静着比动着动静更大
她卧着比走着雷声更响
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想让她不动
可是你们忘了
她身子不动
可是她会唱歌
她的歌声会顺着风飘到十万八千里去
她的歌声会顺着波漾到十万八千里去
是的
会有一天
全世界都能听到
那带着“草方格”的歌声
是的
会有一天
全世界都会迷醉
那带着“草方格的歌声”
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想让她不动
可是你们忘了
她身子不动
可是她会呻吟
她的呻吟会顺着风飘到十万八千里去
她的呻吟会顺着波漾到十万八千里去
是的
会有一天
全世界都能听到
那带着“草方格”的呻吟
是的
会有一天
全世界都会迷醉
那带着“草方格的呻吟”
那无字的呻吟
就如塔克拉玛干的风声
忽隐忽现
忽强忽弱
全世界的身体都能听懂
那无字的呻吟
就如塔克拉玛干的风声
忽大忽小
忽有忽无
全世界的心灵都能听懂
《草方格》之四
你知道吗
一个激情万丈的身体
什么都制服不了的身体
会被音乐束缚住
安静如一个远古的梦
你知道吗
一个热情澎湃的躯体
什么都不肯屈服的躯体
会被幽息制服住
平静如一个幽远的梦
你知道吗
一个狂野不羁的灵魂
什么都不能降服的灵魂
会被一首诗降服
安静如一把月琴
《精绝古国》
真的是你吗
你就在我的身边
在我的经过的路上
在沙海的某个方位
有你的遗址
但我决定还是不去打扰你
我知道你曾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就有一个国家的一切
可是你终是迷失沙海
像一个梦一样
我不知道你国家的人都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都不重要了
反正是大沙漠被你们惹恼了
你们都消失了
一切都消失了
你们的国你们的人
你们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你们的结局是消失了
你们的结局是永远消失了
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
你们了
因为你们已经消失了
因为你们再说什么已经没有用了
《精绝古国》
传说中,
你被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一个古老王国,
你是西汉时期西域林立这里的三十六个王国之
你的大名就叫精绝国
你算是尼雅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王国
传说中
这里离京有一万一千一百二十里
住着四百八十户人家
养着士兵五百人
有官有民有兵有将
你曾是丝绸之路上要塞之一
只是奇怪
丝绸之路兴盛在唐朝
你却在公元4世纪前后
神秘地消失在大沙漠中
来回的商人觅寻你时
你却“千呼万唤无踪迹”
你却“风沙遮面影不见”
你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国”
你却“只知有国不见有人”
西方人只好把你叫“东方的庞贝”
漫漫 2000年
多少人找你寻你觅唤你
你为什么仍不出现
你是丝绸之路的感叹
你是大沙漠的未解之谜
《蜘蛛》
小小蜘蛛
你不就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凭什么你走来
脚步声沙沙
仿佛带着宇宙的颤动
凭什么你走来
小骨头铮铮
似乎拥有战国时期兵器
凭什么你走来
小绒毛凛凛
恍惚背负宇宙大帝使命
小小的蜘蛛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就是来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
你居然想无敌
你居然想横扫一切
凭什么你的足音
足以整动整个地球
任什么你的磬音
足以震撼整个宇宙
你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你的身边没有草
没有花
没有庄稼
没有树林
没有小鸟
没有野兽
不就是没有这些
你是沙漠无野兽蜘蛛称大王
《蜘蛛》之五
小小蜘蛛
你不就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凭什么深夜那么静
你走来
居然正步向我走来
你以为你一个就是一个方阵吗
你以为你一个方阵就是一个军队
你以为你一个军队就是天兵天将
为什么你的绒毛刮擦一下
就如千万将军刀出鞘
为什么你的小腿停一下
就如万万将军弹出镗
小小蜘蛛
你不就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凭什么深夜那么静
你走来
居然正步向我走来
《蜘蛛》之六
小小蜘蛛
你不就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蹑手蹑脚向我走来
走来就是了
干吗要配那么多的音响
你的细足弹响的可是八公山下
你的绒跳蹭响的可是十面埋伏
你水上嘴隐动着唱的可是四面楚歌
你小肩膀耸动着擦响的可是命运交响曲
小小精灵
你蹑手蹑脚向我走来
走来就是了
干吗要配那么多的音响
《蜘蛛》之六
小小蜘蛛
你不就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屏息敛气向我走来
走来就是了
干吗要配那么多的金属声
你细足下磨动的可是钢屑的摩擦声
你绒毛间震动的可是铁丝的弹簧声
你肩膀里回荡的可是银器的嘶叫声
你睫毛隙颤动的可是金子的呻吟声
你屏息敛气向我走来
走来就是了
干吗要配那么多的金属声
《蜘蛛》之七‘
小小蜘蛛
你一个来谈判就可以了
干吗身后调来千军万马
你担心我会扣留你吗
你担心我们谈判会失败吗
小小蜘蛛
你骗不了我
我已经听到你身后的行军脚步声
沙沙沙沙沙沙沙
小小的蜘蛛
你不是声称
你是孤胆英雄吗
你不是声明
你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
我已经听到你身后装备车轱辘声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知道你有无数秘密
知道那些秘密会在某地旋转
知道那些秘密会在风沙中隐现
隐现
就好像是什么爆炸后出现的蘑菇云
也不知道是原子弹还是氢弹
《塔克拉玛干的小屁孩》
他是一个农建师人家的孩子
整个小野人一个
他喜欢悲壮地观看蚊子站在胳膊上叮咬他自己
那瘪肚子渐渐鼓大
最后鼓成一个透明圓球
最后鼓成一个发亮小太阳
他喜欢到小沼泽中去捞鱼
把捞出鱼儿放在手上晒太阳
然后看它们一条一条钻进自己袖子里
然后看它们一条一条掉入自己的裤裆里
然后看它们被放生一条一条重回水里
他喜欢拿着烟纸对准爬出小蜥蜴
看它跳起来舞来
再快快移开
他喜欢追着小蜘蛛
从这丘到那丘
从这壑到那壑
几个小时连续做战
就像当年人们寻找失踪物彭加木的遗迹一般
《塔克拉玛干的小屁孩》之二
他是一个农建师人家的孩子
小屁孩子一个
他喜欢丰收的喜悦
塔克拉玛干的周边
因为有了塔里木河水的滋润
植物变得丰润茂盛起来
在石榴刚红时
他喜欢上树
亲吻其中最红的一个
任红露粘在脸上
在葡萄熟透时
他喜欢站在架下
仰头吃那一串串的果实
任露水滴在身上
在库尔勒香梨没有运出时
他喜欢观察公梨与母梨的区别
并把他们配成一对一双
任梨儿也会心一笑
在大蒜成熟后
他喜欢学那些贩子
把大蒜埋入沙子
等干透了再把它们挂起来
任大蒜也说你好
在青椒、西红杮、黄瓜、大头菜熟了时
他喜欢亲手去摘
然后拿篮子提回家
看着奶奶做出来端在桌子上
他们吃得高兴
就像那菜是他自己亲手种的
在公鸡发情母鸡下蛋的日子里
他喜欢坐在自家柴屋的小篱笆中发呆
看公鸡怎么采蛋
看母亲怎么下蛋
听到母鸡叫咯咯哒
他会第一个蹿过去掏蛋
《塔克拉玛干的小屁孩》之三
他喜欢把馒头放在七十摄氏度的沙子中翁干
然后向带上它向沙漠腹地进军
他以为能看到更多的新奇
可是他越走越失望
他只好向回走
他回到大沙漠边缘的地方
他回到他在沙子中翁干馒头的地方
他回到他在沙子中翁干馒头的地方
决定下一次出发的方向
《塔克拉玛干的小屁孩》之四
小屁孩子必须承认
沙漠无垠但是他有“敌人”
这“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一帮
不是一小帮而是一大帮
不是一大帮而是几大帮
这些“敌人”总认为沙漠是他们的
一见到小屁孩子
“敌人”就追打
一遭遇“敌人”小屁孩子就疯跑
那一天小屁孩与小伙伴去鱼塘玩
正玩得起劲“敌人”包围过来了
喊着小屁孩子与小伙伴们听不懂的话语
打着小屁孩子与小伙伴们看不懂的手势
小屁孩与小伙伴们唯有一个武器
那是一辆山地自行车
小屁孩子与小伙伴们都跳上了
那辆狂奔骑行的山地自行车
与追过来的“敌人”激战
与扑上来的”敌人“ 鏖战
小屁孩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一脚踹倒一个追来的“敌人”
二脚踹倒一个追来的“敌人”
”敌人“终于稀里哗啦
倒下一路
像馕在馕坑中翻滚
小屁孩子抛出一个飞吻
脸上绽放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嘴里也说出一串自己都听不懂的话
”呜哩哇啦“
小屁孩子可不是土著
他的身后是说不同汉活的兵团人
进疆多少年仍不会说一句土著话
江浙人恰恰恰
河北人哈哈哈
广东人拉拉拉
河南人啥啥啥
云南人可可可
东北人嘎嘎嘎
最独特是小屁孩子在玩
他身后有一个上海女人
像画屏美女一般攀着花枝
说出一口上海话
说自己不惑之年仍未嫁
妩媚地瞟我一眼
仿佛我是那个她错过的他
《小屁孩子的混蛋逻辑》
小屁孩子是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子有小男孩子的逻辑
一个没有”敌人“的小男孩怎么能叫小男孩
一个没有”敌人“的小男孩应当叫叫女孩子
这就是那个小屁孩子的混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