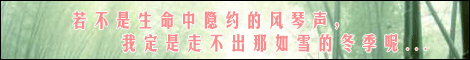更有一种许多人的共同的独特的感觉,那就是面对葛水平时,如同面对一个潭,看起感觉那水出奇地平静、那波出奇地宁静、那浪出奇地幽静,那涟轻飘地扩散,那漪淡淡地柔美。可是面对这个潭,你却有一种莫名其妙地害怕。深望这潭,你却有种莫名其妙地恐怖。细想这潭,你却有种隐约地不安。你猜不出,是不是某次台风飓风野风是从这潭中吹出。因为,越是平静,可能越是不平静。越是安静,可能越是蕴藏着不安静。越是幽静,可能越是藏着某种不测。越是轻飘,可能越是蕴涵某种神秘未知。越是柔美,可能越是含着某种深不可测。可能不仅是鲁十一,而是所有接触过葛水平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甚至是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都变得有所顾虑,有所担忧,有所恐惧。因为,你不知道这潭有多深,你不知道这潭中深藏着什么?是鱼?是虾?是大鲵?是蛇?是仙女?是精怪?是怪兽?是恐龙?是魔鬼?是怨魂?是幽灵?是吉祥?还是不祥?你不明白那水为何会那么静。你会奇怪那水面为何那么服帖。你会好奇那水会那么柔顺。那睛天才有的钻石滚动声,那雨天才有的珠玉滚动声,那雪天才有微妙叹息声,那雷电天不知道珍藏在哪里的小鸟的某个叫声。那深夜才发出的奇妙乐声,是自杀小姑的叹息?是枉死小媳妇的哭声?是深山两种队伍血战的撕杀声?是深山大墓发出的呻吟声?感觉那潭那么深邃幽静美不胜收,可是心里却有一种隐隐地担心,因为那中仿佛有着一种强烈的收魂摄魄之气,特别是深夜这美潭仿佛蕴藏杀气、冰刀、寒剑、鬼瓜、魔手、阴气、怪响,仿佛要把某个人某种人某类人抓进去,吸不去,仿佛收一些命,连血连肉连骨都找不到,对于这样美丽的漂亮的潭水,也是平平常常,平平静静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它让我想起我的大巴山的那个乌潭,那神秘的收了多条命的乌潭,让你望一眼,还想回头再望一眼。那水中深蓝中隐现着碧蓝,碧蓝中动现着晶蓝,让你忍不住走了好远,再回望一眼。我的妈妈山的人都说,那乌潭是没有底的,是与地下的什么暗河是通的,是与远方的什么湖是相连的。还有人说它可通到四川的万源去。没有人知道它有多深。没有人知道它能走多远。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故事出没在这的美潭,有几多幽灵萦回在这灵潭,更无人晓得有多少传说回荡在这碧潭。
我们看看葛水平在自己的博客访谈中怎么说,看看葛水平是怎么样看亲人们融入乌潭,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乌潭的一部分:“多少年后,我看到我亲人们的笑容淡淡的轻得像烟,我站在老窑的门槛上望他们,看他们犹如跌进一潭深水,慢慢地淹没了他们的笑容。斑驳的墙壁竖立着,积灰的老窗合拢,迈不动步,深远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涌现,我突然觉得生活的意义再次变得恍惚,变得不可确定,因为,活让我至亲的人远去。我有情债!他们给了我朴素的底色和对自然的无限敬畏。”
起因,难道皆因它太平静了,平静到太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了?
野人竹子快讯:近日葛水平编剧的路遥《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正在隆重推出。葛水平与后面冒出的总编剧就版权署名正酝酿一场风雨世纪官司。
(草稿正起思路正开谢绝一切形式转载与推广)葛水平的《祼地》上架。我同意某人的观点:有创造性与个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小说美学品质,在卡夫卡是一种“恐惧”,在米兰·昆德拉是一种“智慧”[16],在鲁迅是一种“反抗绝望”。但我不同意某人的观点:善良是葛水平的生存观念与创作理念,是她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
评价葛水平用“善良"来概括之,太轻浮、太简单了、太表面、太不深刻了。葛水平的生存观念与创作理念当是一种“大善”,大善包括善良;但是这个“大善”包括很多,却不是简单一个“善良”可概括。
不好啦!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和《牵手》大导一同被原始酋长蛮荒野人部落抢劫!联手推出第三首歌《走进荒漠》
葛水平自己也说“上善若水”。可是这个“善”与“善良”并不是一会事情。
连葛水平自己都说“丑”是一种进,“善”是一种守。由此可见,葛水平的善是一种守。就如水被山挡时,可以沉默,可以低头,可以屈服,可以弯屈,可以匍匐,可以扭曲,可以忍胯下之辱,可以受割腕隐疼,但最终的目的却是在不断地寻求突破。
那是一个水平线,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线。这个水平线有时是整的。
就如当年红卫兵杀一路,毁一片,砸一通,可是支撑他们的力量居然是一种“大善”?一种解放全人类,一种破四旧立四新,一种同情底层百姓,一种幻想中的人与人平等的蜃景?一种民族将毁灭的恐怖感?一种扭曲了的正义感?一种中华民族想强大的臆念?一种当时老百姓公认的不破不立的大善理念?一种膨胀的英雄主义幻想?一种释放的渴望展示的性能力?一种全方位释放的大爱?一种幻想理想公平的臆症?一种老百姓担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人头不保的歇斯底里?无助心态,一种对能人对曾经是法人的整体嫉妒整体恐惧?一种因部分黑心富而对富人价层整体的仇恨的弥漫?一种洗脑后必然出现的蝗虫现效应?一种个人崇拜后终将出现的“群聚反应”?一种家族权术扩散到整个民族形成的毒气蒸发?一个民族被压抑太久后释放丑恶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真要再起意念中鸣起的尖音?一个国家从低谷再次挣扎爬起必须精神苦难之旅行????当时的红卫兵除了被“神权”赋予了选择的特权,更仿佛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他们可能全国各地免费串联,他们可能充分享受的青春的解放,激情无法释放就释放在对付“走资派身上”,他们充分享受自由化的无限扩大,还感觉不自由,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破坏文明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甚至形如初尝腐化的滋味自以为是上一辈“英雄们”的滋味。正是这些理念支撑着这些小将一往无前,砸毁文物,鞭打掐尖,杀人如麻,激情碰撞,摧枯拉朽,山崩地裂。小将们根本没有想到毁灭的却是中华文明。那么这个大善中就有深刻的东西让我们去思考去分析去解剖了。
葛水平的“大善”决不是“善良”,而是探索这种“大善”形成的中深刻的道理是什么。寻找一个民族整体迷失或是整体前行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比如日本鬼子仅南京就屠杀三十万中国人,是什么支撑这个大和民族在那些瞬间变成魔鬼?我曾看过一部日本导演宫奇峻动漫片子《龙猫》,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那样重视家庭亲情那般友爱,一家四口的普通亲情让人反复回想。可是为什么变了呢?一定有一种日本人的“大善”理念支撑,不然不可能让好好的人变成杀人机器、杀人魔鬼、野兽都不如怪物。是不是某些日本人也在一种恐怖信息的恶梦梦靥中。那么是什么?比如日本将亡?比如日本人种将灭?比如世界将毁?比如海啸或是地震将食日本?是不是人口膨胀的恐怖?是不是经济危机的恐怖?比如为了大和民族必须毁灭支那国?比如几千年想侵略中国的日本祖宗潜意识终于使然。比如二千年皇权近亲繁殖丑曲毁灭前集聚的“核能力”。比如鬼文化比如日本祖先一代一代埋伏下来吞侵中国的野心终于汇流勃发?比如,二千的年的皇权无大的变革,一种整体人性渴望突围群魔从身体中的突围?一种压抑千年兽性的大释放?本我的恶性膨胀?等等。
比如淮海战役,是什么使得几百万农民推小军去支援解放军?如果没有在大善理态的支持,旧中国如何被推翻?新中国如何能够建立?中国的组织生产的原中层怎么能够被渐次毁灭?别忘了当时的军队的比例是少的胜了多的,山野中的打败城市里的,已经被国际公认的被老百姓公认的打败。
那是一个水平线,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线。这个水平线有时是碎的,断在滚滚红尘中,碎在茫茫乱事间,你要会觅寻。你会发现葛水平笔下的人物虽然各异但是那个恪守线却恍惚从一根大线上隐遁下来,从一根大线上断裂下来,从一根大线上切分下来的。
好消息,新浪微博以头页头条的重要位置隆重推出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和《新亮剑》大导杨阳合拍的歌曲《走进荒漠》据悉,两位歌手与全部演员均来自真正的原始酋长部落。所有的群众演员均是真正的吉卜赛人。恐怖呀!敞怀唱大风的已经鬼魂化的肖复华加入其中........这些碎下来断下来的老百
姓的水平,你去悟,不论它们如果变幻万千,不过是遥遥远远那一线大山小山的屈服线,老百性恪守到不得不低头的生存线。
只不过是葛水平在取材上更重选择一些“表面向善”的题材--葛水平显然是客观的,她恍惚想先用大善为她的作品获得一种博大的气场:比如她想写抗日孤身打死许多鬼子的小男孩,比如她写被拐的弱女子以哑默默抗挣强权,比如她想写与帮活男人们乱性的母亲心中的真正深爱自己丈夫与儿子的隐衷。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葛水平的生存观念与创作理念和她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细细感悟,这些个体的格守线正是从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线上掉下来的一段。
更有大山中女儿们的真心态,进“山”的人虽然不少,能进入的男人女人并不多,虽然有些人是女人,也不见得能走进自己。多数文人骚客更像是融着靴骚痒而已而已,即便是许多的名著,除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少有几部。但是看葛水平文字时,却感觉有一个小小女子,平静地安静地宁静地,秉烛游进在那幽暗的九万九千九百九十米的曲折萦迥的愁肠中。让人联想到华严经中句子,“譬如一‘小烛’入于暗室”,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百千年暗悉‘恍能’破尽”,但,终是感觉,那个小烛,真的已经进山,真的已经在山洞中游移,虽然那小烛偶尔幽微火花一爆,如同那百里千里万里曲拆愁肠中蠕动的一个小小寄生小虫儿身子一亮,照亮那肠壁上古画,肠壁上像形神秘象形文学费解,更有那肠壁上古窑洞里幽鬼谧地扑朔了一下又不见了,留下的尽是斑驳残画,沧桑遗美,触动我们脑迴或肠道中熟悉的什么。但是毕竟是亮了一下,让我们感觉到那些幽怀一古的东西长长地存在着,感觉到那个小虫儿在里面长长地行进着,带着独属于小虫儿的好奇与灵气,带着水本身的真香与真气,在其中移动着。
葛水平笔下的女人虽然形态各一,可是细细着琢磨,却均是在老百姓女儿生存线的上下挣扎。而葛水平诠释的绝不是一个“善良”了得。而是这些老百姓女儿的生存线。葛水在感觉这个若隐若现的老百姓儿的生存线。探索在各种的情况下,和种压力下,各种外力下,各种风向中,各种强权下,各种状态下,老百姓的女儿们会如果去做会如果求生。
怎么是一个简单的“善良”了得?
葛水平笔下的女主人有悲天怜人的也有乱情乱性的,有正气浩荡的,也有小人性卑微的,有为自克人的,有为自收命的。但更多的只是屈服生活嫁给穷人的少奶奶,委曲当小平静生活的小太太,被抢做妻的落魄凤凰,手推车送来的神秘女人,被大善压抑给驴喂奶的婶婶,不得不屈服自己唯美追求的普通女人,被理念扭曲报复“仅是未婚夫”而非“爱者”的老姑娘,被拐买人进山变为哑巴的弱女子,进城进不去、回乡回不去的彷徨城乡之间的剩女,为了生存下去和每一个帮活的男人乱沦的孩子的妈,等等。
这些人身上恪守的低头线,看似碎的,但是你细想,其实是从一条线下截取下来的,一条老百性的恪守线低头线上碎下来的。
葛水平似乎是在观察又似乎在做试验,想观察老百姓承受的压强变化到不同的数值时老百姓的身上的“物理变化”或是“化学变化”。正如大作家莫言所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正如人民文学李敬泽的提法:小说家当做一个人性的鉴赏家,为那些难以言喻的一切找到表达的形式。--这里“难以言喻的一切”当然包括美的,也包括丑的。而似乎这种“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才是葛水平关注的重点。
这更进一步窥探葛水平的“汉字方方正正,我们做人也要方方正正”,“追求一种大善理念”指的到底是什么。
是的,你想想,汉字怎么写,凡是中国人都会知道怎么去写,但是少有人感悟怎么去写。这是一个普通的规律,个别的只是字体不同,不论你用甲骨文、篆书、草书、行书、楷书、隶书、狂草,甚至你用中国民间的鸟语、袖子语、黑话,只是表达直接或间接表达汉字意思的,但的确是有规律可探寻的。就算是有些我们现代人还没有破译某种汉字。就算是某些人均写一种体比如草书也是人各有体,也是有规律可寻的。也就是字体形状均属个性,但是写法却是有规则去探,有规律可寻的。这可能才是葛水平说的那个“汉字方方正正,我们做人也要方方正正”?
葛水平的“大善”并不是“善良”而是探索形成这种民族心态中深刻的道理,而真的是人性的“物理变化”与“化学反应”的普遍规律。在某种情况下,人变魔鬼、人变仙女,抑或是魔鬼变神仙的内因与外因、魔鬼变君子的原因或是原理。
葛水平的“大善”“上善若水”是包涵的善良,但同样包涵丑恶、虚伪、阴谋、虚伪、诡计、算计、智慧、谋杀、绞杀、屠杀、暗算、吞食、毁灭、执拗、自私、公心、救助、家族、繁衍、大爱、大丑等一切用于社会人的名词或词组的。
让我们听听葛水平自己在博客中怎么说:
“我们该明白,他们的日子不是这样永远的恬静,庄稼不出青苗的时候,他们会为了一渠水引到自家田头而大打出手,也会因为谁家的牲口吃了庄稼因小生出大事,人不可能舍却作为背景的生存,活着,谁都会为了保护自己活着的简单口粮而争斗。我们不会像河流那样默默伸出自己,放弃所有,克制欲望,善是做人的底线,决不是不沾荤腥。恶呢?哲人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一份必定要背着的邪恶让人性投向了深褐色的黄土。”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平淡行进的生活,让我去向不明,创作的价值还需要朴实的思想为支持,我必须坚强到成为一个顽强的人,然后,我才能进步。”--这正是说明丑与美,善良与丑恶,均有规律,但对于太过渺小的个人又去向不明,葛水平告诫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社会的真实断面,否则便不能进步?
“ 一个话语谈不上“权”的人,是无力控制和调节自己写作走向的,跟着时代走,走哪写哪。我不想虚假的说我坚持或坚守什么写作立场,立场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我写我的小人物,小手艺,小河流,我对科学上的确凿和精准不怎么关心,如同不关心政治一样。我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也决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也并非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我更不是直轨上的车,只是那些好像离我很远。写作的人除了保持文学性的同时还得保持社会性,我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是我。”
更让我奇怪的是葛水平的语言。那恍惚是一个她自己的语言,感觉多少说多少,感觉很贴切--仿佛是纯棉内衣一让人感觉舒适,像真丝睡衣一般让人感觉贴切。那是一种从没有过的词的组合,句的组装,让人由不得不惊奇起来。一种从没有的词的组合,句的组装,在波光水谲中神出鬼没、柔肠百转中云雨缠绵、在多姿多彩间飞针走绣,在老屋古木间灵魂隐约,在古雕陈香中吾自诠释的仿佛是一种东方式的性感。一种隐而不露密而不宣的东方式性感,带出更大的神秘毁灭力,萦绕其间。不论是从哪个角度,金莲也好,兜肚也好,喊山也好,哑巴也行,绣鞋也好,旗袍也好,对襟也好,居然都可颤颤悠悠地落在上面,风花雪夜上面。且有一种东方隐美的女性性主动,方式是从没有人落过的方式。
但是更大的神奇在于,读的时候感觉那语言千般的好,万般的美,古色古香的,回味悠长的,可是想的时候却一句也想不起来。想重复时,却恍惚只有些摇曳的句子,鱼儿般从过去的岁月中游去过,想看清时却梦般逝去,居然是一个细节也讲不出来。居然是一条鱼儿也无法用嘴来复述。甚至是那些对话,读时感觉万般贴切的,可是却是不能拿来重复的一般。那些句子都是柔进了女的灵性与悟性与感性的。仿佛是无论谁都不能重复的独属水平的语言。
“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从远处望去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壁上下,绕着几丝儿云,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瘦得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
“八月十五过后,时间像缩了水的绸子,比起夏天呢好端端短了一截。吃毕晌午饭时分的暴店镇,远看过去街道如同伸展四脚的牛一样慵懒。”
这是小说句子,还是奢侈诗句压缩在这里?
读者只是知道,那是美好的女儿家的房子,恍惚是千古万年之前的墓地间的蜃景,民间的梦中土窑,你走进去过,且有过那么一种特别的感受,让人流连过,让人神往过,却不能复述。
再次回望,还是那感受,一句也想不起来,一句也说不上来。
能让人记住的,只有那上世纪的绣图,有那上世纪的古屋照,有那上世纪的老木衬,有那上世纪的砖雕底,有那上世纪磨盘陪。只是那蜃景在荒草墓地间倏忽即逝,恍惚与这个世纪有,但又不再重现。唯留下上世纪的氛围,这世纪的迷惘,在脑海中鱼一般流连。真个“真水无香,假水有妖”!
当然,还有一个能记住的,是葛水平的小说总有一个精彩的结尾。比如《天下》的结尾处的“李满堂小学”。如《玻璃花》那个老姑娘最后舍身报复,且是报复一个老姑娘并不爱的曾未婚夫,等。那结尾如同葛水平的“我们做人也要方方正正”是可令人反复回味的。就算某人不肯反复回味,葛水平也有本事让你合了作品后,仍有闪电一次一次在你不经意时以葛水平的方式击打你。这也是葛水平小说最精彩的大手笔。
能让人记住的,还有那堆风花雪夜中突破而出的一个强烈的女声:“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强烈得犹如远去的父亲的招手,‘我知道我必须即刻上路了,要沿着一道迢递之路走进那些往事。我要尽一个世俗人的眼光来写他们,‘世俗’是我的命中注定!”
发光是是那些那上世纪的玩艺儿,什么兜肚什么三寸金莲,居然诠释的不是女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却似是男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理解。
而人物,也恍惚不是村里女人看到的而是村里男人透过时光看到的那个仍靠在屋檐下针线的婶婶、东家床上一团雪白肉的小妾、可以抢来抢去的坐在小车上的女人、被村里人关注被村里男人向往又恐怖着不敢拥有不敢持有大龄女人、可以不再挣扎终于听从男命的小妇人、被人贩子贩来贩去不能反抗社会只能以不说话反抗的“哑女”。等等
恍惚没有细节只有意境一般。
恍惚只有一句却不能让人记往一整句一般,仿佛没有明晰到让人记住的对话,除了老百姓的一些口头话,仍是来自老百姓却无法还给老百姓,分不清哪一句是当记住的。恍惚没有对话,只有一种美的感觉,只有一种优的感受,一有一种雅的回响。
《走进荒漠》,《牵手》大导携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去原始酋长蛮荒野人部落觅寻野人风过的痕迹。
只是这中的某些大众组成,成为一条老百姓的水平线时,葛水平就在那里了。
而葛水平之所以可能得鲁奖,正是因为她曾被生活打入底层,曾被生活卷入底层,加上她能水般无我,于是她能体悟、能体察、能描述、甚至能看见那个“老百姓女儿的恪守线”。
这也是老天爷赋予被生活打入最底层被自尊蹂躏过女儿特别灵性。
正说葛水平博客中写的:他曾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多好的话。
而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情什么态,均波澜不惊,只是好奇地探索这“低头线”,思考这众山低头的道理,探索这众山“匍匐在地”内在的恪守。这让我想起人民文学李敬泽的新鲜论点:小说家当做一个人性的鉴赏家,为那些难以言喻的一切找到表达的形式。《红楼梦》是探索人性美的巨著。
那同样一种如同大巴山野人毛竹的“无我”状态。
所不同的是,葛水平喜欢把自己置身在这个民族“大善”的水平线中“无我感受”“无我感悟”“无我感触”“无我感知”。而毛竹刚是无所不在,那是另一种“无我”,一种原生态写作。
葛水平的“上善若水”,是指水经各种神秘力量泉水一般涌出,溪水一般流出,清澈地汇合,但是中游却不能不接纳的一切“外因”,下游却不能不包容的一切“污染”。我想葛水平只是探索那条入海的水,从源头探起,故而称“上善若水”。
葛水平出现在的“大善”水平线那里,尽量无我地感觉山神凹老百性的“水平线”才是对葛水平的终极评价。
无我,所以葛水平可如鱼一般在山的地气中游来游去;
无我,所以葛水平可如蛇一般在山的地缝中钻来钻去;
无我,所以葛水平可如小虫儿在山的土地中神出鬼没;
无我,所以葛水平可以小溪一般在山神凹蹿来蹿去;
无我,所以葛水平能善能丑能恶能美能淑女能妖精能魔鬼能巾帼;
无我,所以葛水平才能在那里诡秘地多情,神秘地无情,摇曳着风情,精怪地多情,无原则地深情,无帮助地痴情,无底线地善良,身不由由地丑恶,像鱼儿一般出没在一个深潭中。
无我,所以葛水平笔下的女主人公才能在那里高贵中残杀同类,残杀同类中表达善良,捕捉不住那多种摇曳生姿的如水女儿心态的涟漪,荡漾出女儿们的水平线。
无我,所以葛水平可以把自己理解消化后的美理想化的美停留在停驻在山神凹“大善”水平线之边,那一个一个逝女、遗女的幽灵魂魄之线上飞翔来飞翔去。
更有一种许多人的共同的独特的感觉
更有一种许多人的共同的独特的感觉,那时是面对葛水平时,如同面对一个潭,看起感觉那水出奇地平静、那波出奇地宁静、那浪出奇地幽静,那漪出奇地柔美。可是面对这个潭,你却有一种莫名地害怕。深望这潭,你却有种莫名的恐怖。细想这潭,你却有种隐约地不安。你猜不出,是不是某次台风飓风野风是从这潭中吹出。因为,越是平静,可能越是不平静。越是安静,可能越是蕴藏着不安静。越是幽静,可能越是藏着某种不测。越是柔美,可能越是含着某种深不可测。可能是所有葛水平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甚至是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都变得有所顾虑,有所担忧,有所恐惧。因为,你不知道这潭有多深,你不知道这潭中深藏着什么?是鱼?是虾?是大鲵?是蛇?是仙女?是精怪?是怪兽?是恐龙?是魔鬼?是怨魂?是幽灵?那深夜才发出的奇妙乐声,是自杀小姑的叹息?是枉死小媳妇的哭声?感觉那潭那么深邃幽静美不胜收,可是心里却有一种隐隐地担心,因为那中仿佛有着一种强烈的收魂摄魄之气,特别是深夜这美潭仿佛蕴藏杀气、冰刀、寒剑、鬼瓜、魔手仿佛要把某个人某种人某类人抓进去,吸不去,仿佛收一些命,连血连肉连骨都找不到,对于这样美丽的漂亮的潭水,也是平平常常,平平静静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大惊上怪。它让我想起我的大巴山的两个乌潭,那神秘的收不多条命,有许多故事的美潭,有许多传说的碧潭。
---不说远古,不说近古,只说近代,我知道的,我的大巴山,那溪水间不起眼的乌潭,已经有两个有名有姓的人自杀于其中。真难以想像,我大巴山的乌潭,我每一次路过,都数次回望,惊叹于它看起来,那么清那么浅那么静,就连其中层层水纹,虽隐现着,看起来仍一眼见底,水纹道道深深浅浅,却是道道可数;水底石崖石砾,却是历历可见。其中一个是爸爸生前在青海一个大巴山老乡的聚会上,他们在说,说某某某,自杀了,乌潭边有一堆烟,可是能是自杀前在潭边坐了很久,想了很久。另一条命,是我的某房外爷家的一个仅20岁出头的儿媳妇,有人看到她就跳进去了。为了这个媳妇自杀,娘家来了近千人来二外爷家来打人命。上一席,轰轰烈烈吃完,碗碟全部砸了。再上一席,轰轰烈烈吃完,碗碟全部砸了。为这了个自杀的年轻的媳妇,二外爷,这个打了无数赢官司而出名的外爷,这个与堂堂赵乡长打三场官司场场都打赢的二外爷--大巴山有俗话“赵莫惹,唐别粘,惹了赵家喊皇天”。可是二外爷与赵惠生打一场赢一场。赵乡长不服,层层上告,解放初,两家的官司已经打到高级人民法院。外爷被当地人称作“咬铜吃铁”人物,外爷当乡队副多年一呼百应居然几次组织民团打败棒佬儿王三春。王三春是大巴山自卫行团都不敢打的强梁,是中国近代十大土匪之一。王三春杀人如麻。大巴山不知道多少商人掌柜死在王三春手中。而毛竹祖祖徐文美之死,可能就与某房二外爷打赢王三春有关。
我某房二外爷披麻戴孝像送亲老子一般以隆重仪式送葬自己的20岁出头儿媳妇,仍不解娘家心头之恨。大巴山有人说:大巴山终于有人把你那房二外爷稍稍配治了一下!
而巴山乌潭不止一个,每一个乌潭都收过数命,都有数不清的故事。
每一次路过,我都数次回望,惊叹于它看起来,那么清那么浅那么静,就连其中层层水纹,虽隐现着,看起来仍一眼见底,水纹道道可数;水底石崖石砾,却是历历可见。
面对葛水平时,如同面对一个潭,看起感觉那水出奇地平静、那波出奇地宁静、那浪出奇地幽静,那漪淡淡地柔美。可是面对这个潭,你却有一种莫名地害怕。深望这潭,你却有种莫名的恐怖。细想这潭,你却有种隐约地不安。因为,越是平静,可能越是不平静。越是安静,可能越是蕴藏着不安静。越是幽静,可能越是藏着某种不测。越是柔美,可能越是含着某种深不可测。可能是所有葛水平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甚至是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都变得有所顾虑,有所担忧,有所恐惧。因为,你不知道这潭有多深,你不知道这潭中深藏着什么?是鱼?是虾?是大鲵?是蛇?是仙女?是精怪?是怪兽?是恐龙?是魔鬼?是怨魂?是幽灵?那深夜才发出的奇妙乐声,是自杀小姑的叹息?是枉死小媳妇的哭声?感觉那潭那么深邃幽静美不胜收,可是心里却有一种隐隐地担心,因为那中仿佛有着一种强烈的收魂摄魄之气,特别是深夜这美潭仿佛蕴藏杀气、冰刀、寒剑、鬼瓜、魔手仿佛要把某个人某种人某类人抓进去,吸不去,仿佛收一些命,连血连肉连骨都找不到,对于这样美丽的漂亮的潭水,也是平平常常,平平静静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揭秘:葛水平的老师是谁?
一路走来,葛水平要感谢阎法宝和程画梅两位老师,我用“德高望重”来感谢他们二位。他们的摄影作品充满了动势,有我感觉的延伸,他们为沁河两岸的山水建筑打开了一个艺术的世界,那个世界里艺术有多么的无奈,一些渐行渐远、再也无法伸手把握的山水建筑,让我明白了生活的细枝末节通过平实的镜头语言铺陈出来时,岁月有多么静好。
我要感谢杨军和赵宏伟两位老兄,他们往常温良恭俭的色影风格在沁河两岸的照片中变得老辣纵姿。现实生活中他们如此热爱民间,他们的作品中有空灵酣畅的韵致,将停留在古典情结的某种表述方式加以当代公共话语的重新解读;而流溢在画面上跃动、朴实、浑厚的各种色调,又将民间的美提升了一种格调。
我要感谢何晨,给我的一路增添了生活趣味,而他的摄影他叙述生活的文字风格必将有益于我以后的创作。
我还要感谢孙喜玲和王春平两位老师,在精神上给我引领,多年的友情让我的行走姿态因为他们的出现让我有了别有一格的生命姿态。
好了,接下来我感谢沁水籍老乡郑建国先生,他对我的帮助我在此鞠躬谢了!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宣传部长王玉圣先生,是他给了我更多的理解让我行走!
最后我感谢亲爱的赵学文和陈洋和张永文老师,感谢你们熬油点灯为我这本书付出的辛勤劳作!(选自葛水平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