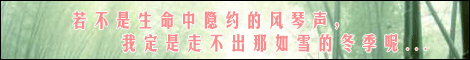第一辑
——迷失在西部
哦!这盐花,这苦涩的琼花!
许是汗,许是泪,许是血……
许是希望的结晶,许是幻想的凝固,许是痛苦的演变……
迷失在西部
——青藏公路沿线采访散记
到戈壁滩去!心里知道,唯有它可以溶化生命中那泛滥的激情,唯有它可以使我回返尘世时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顺着茶卡盐场的几排平房跑了出去,天已微亮,便沿着柏油路向戈壁滩跑去。戈壁滩上稀稀点缀的骆驼草渐渐被朝霞染成血
红。四边的山由于外亮内暗而产生一种逆光效果,仿佛四堵万丈城墙。朝霞由血红渐渐转向阳红。有一块黑云先是在“南墙”后漫卷,继而向“东墙”弥漫,仿佛是战场的浓烟。
“浓烟”很快就把朝霞给遮住了。失望之极,不禁转身,背对东方,加入西部苍凉,空旷。怅然之际,忽发现西边“山墙’之上,从天地交合的一极点,发出一种耀眼的白光,白光忽大忽小,倏地从那极点射出数十条带状玫瑰色光。光带由窄渐宽、由淡而浓,灿然直射中天;光带似由亿万根纤维组成,忽明忽暗、左右转动,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光源似是“山墙”后的光聚成的一个焦点,光线似是阳光由白云折射而来。光源与我似万里之遥又似近若咫尺。一朵朵棉花般白云与“女墙”被镶上红,黄、绿的光边,美丽得让人恨不得热泪盈眶——似乎西边也有太阳要升起。
忙转身望东方,只见太阳仍被黑云遮住,唯有一点红在黑云中隐动,似在挣扎,终于挣出一团红。那红伸缩着,沸腾着,数十条阳红光忽一下从黑云洞中射出。光线丝丝缕缕。光带慢慢地长、渐渐地宽,与西边的同样壮观。
两边的光带交织出一个角度,上空闪着一种白光,犹如一个巨大钻石上隐现的光。不由地想起人称青藏高原为世界第三极,难道这白光就是所谓的“极地之光”?
在青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西部奇景,整个人竟呆在那里,不能言语。神秘莫测的西部啊!难道定要我想象古战场的厮杀声、金属碰击声,方能配合这奇景?难道定要我一个纤弱女子把“城墙”上那一个一个凸出部分想象成一个一个扒着“城墙”身体空悬龇牙咧嘴肌凸筋扭的勇士们的一双一双手,一双一双扣进山岩鲜血淋漓的手,一双一双扣着生死界限的手,方能溶进这“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宏伟气魄?
这时“东墙”像平放的手风琴拉开了。那是连绵的祁连山啊!有条金色的河缓缓向这边溢来;金色的山头绵延无际,越远反越清晰,仿佛通往天堂的梯子。 “西墙”也手风琴般拉开了,那遥远的山脉可是分开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柴达木
盆地的阿尔金山?还是宏伟的昆仑山脉?山头上紫烟笼罩,一团团玫瑰色的云从山上升起像无数个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使人怀疑飞碟是从这起飞。
阳红与玫瑰红慢慢地湮散、交织,渐渐地汇成一种颜色。转着看了几回,就分不出哪方是东方了,更辨不出哪个是真正的太阳,我完全地迷失了,只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辉煌的世界中,恍惚走回生命孕育时最神圣的那一刻。
啊!太阳是永远遮不住的!东西两边“出”太阳的奇迹竟是天地之大美,那是一种我是地之心,宇宙之心的感觉。只是原地转了看这边又看那边,仿佛自己是一个地轴,不断伸长的地轴。不是自己转而是地球旋着我转,不是地球绕太阳转而是太阳绕地球转,更确切地说是太阳绕了我转。有一种地磁音在天地间回荡,似乎是我头上的白光发出:又仿佛是我被往瓷实里铸造的声音,更仿佛是西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黄教嗽嘛的诵经声。一时里感觉大地都在音响中战栗。
真后悔没带照相机,真后悔呵!
渐渐地,我进入一种“接天地之气,入无我之境”的奇妙境地,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感觉,仿佛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原来大自然做事是这般执拗,这般不计成本,这般不惜代价。一种不可名状的畏惧,崇敬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哦!若不遵循大自然的规律,阻止它的发展方向,就等于让大自然蕴酿一种内力,积蓄一种能量,这力量是既可能创造世界又可能摧毁世界的。就似这太阳,哪怕是变一种形式,它仍是一定一定要升起的。原来压抑是创造奇迹的真正动力。
原来大自然的力量是这样的不可抗拒,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呵!如同这不论经历多少风雨依旧要向东转的地球;如同那条无论遇到多少坎坷仍执意向东流去的黄河;如同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海子之中的那些裂尻鱼——无论人类在季节
河中投下多少雷管布下多少罗网,无论季节河中有多少同伴的尸体、鱼骨化石仍旧要一年一度地不屈不挠地结成大包(鱼团)冲向季节河的激流中产卵……
一首大自然奏起的交响曲在风沙的呼啸声中隐约可辨。
海市蜃楼
——青藏公路沿线采访散记
茶卡盐场的路像一长串呼呼燃烧的火苗子;茶卡盐场的太阳像一个近在咫尺的烧红的烙铁。“怎么样?”老严的嘴角浮出一丝顽皮: “我们这里可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一阵朗朗的笑震得空气直冒静电火花。
盐湖亮闪闪一片,大老远就能听到水汽哗哗的蒸发声。蒸气再被阳光一照,多少个光圈虚幻着,多少种色彩缤纷着。透过那清澈湖水可看到玻璃般湖底,那湖底被阳光折射出各色莹光,使湖水越发显得晶莹剔透。那漫反射光被水中的、雾中的反射光再反射,形成那么一种迷幻的氛围。采盐工的身子都来回晃动、上
下飘忽着,采盐船忽隐忽现,宛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仿佛几十个酒神仙在一轮隐现的月牙儿上举杯且饮且舞,醉得飘飘逸逸。他们有些在追逐那漫天的彩泡泡,有些戏耍于千层珠帘之间,有些悠闲地玩着那一轮巨大的太阳:一会儿将它
顶在头顶,一会儿把它扛在肩上,一会儿将它当羽毛球打来打去……
看得痴了过去,这些盐工,多浪漫叫!这幅 “毕加索作品”,真够味!犹如湖面上一幅海市蜃楼。
走到湖边,便去掬那湖水,却被老严喊住: “尔想自杀?;这可是杨白劳自杀时喝的卤水!”我疑惑: “那盐工不小心掉进去不就没命了?” “那就只有把盐工送到卫生所喝豆浆,在人肚子里做豆腐。”我们忍不住“扑哧”一声都笑了: “真做豆腐?” “对!” “能救活?” “能!”
站了一儿,已感到水雾氤氲,那是一种生涩的令人窒息的盐腥味。
一个一个采盐工从靠岸的采盐船上往下飘,忽悠忽悠地挣出海市蜃楼。看清了!男的!女的!那一张张脸竟是可泊的阴阳脸,这是由盐的漫反射光造成的,这漫反射光是草帽、口罩都遮挡不住的,它是从四面八方射到人脸上的。那一条条因长期水中作业关节变粗变僵的腿插在一双双盐渍斑驳的雨鞋中,一股股橡胶味在闷热中隐动。那裸露的手上,胳膊上画满一圈圈盐渍,仿佛是古树的年轮……
握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感觉那轻疼的摩擦,我终于有了一份真实感。以前曾多次想象过采盐工作条件的恶劣,却从没想过是这种程度的恶劣。一股苦涩漫上我的心头。那生盐味儿,仍在蒸汽中弥漫。他们定是不知退出苦涩呈现在人眼前的竟是一首诗;他们定是不知道这么艰苦的劳动场面旁观者看着却是一幅画。
我脑海中飞快闪过在察尔汗盐场,柯柯盐场与这(茶卡盐场)看到的状如珊瑚的盐花,形如雪花的雪花盐、宛若珍珠的珍珠盐,钟乳盐、蘑菇盐,水晶盐”。
我更不明白为什么那晶莹剔透,那绮丽多姿是那样深邃神秘,是那样难以捉摸,耐人寻味。 我们沿着绵延的盐山根走上铁轨,又沿铁轨走向盐湖深处。者严慢慢儿向我打开了话匣子:
50年代初,他们一帮年轻人来到了这片荒无人烟的黑色盐漠。这里除了盐漠外围苍茫戈壁滩上生长着稀疏的“有水有阳光才是草,无水无阳光便是刺,根须达十几米”的骆驼刺以外,几乎没有植物,这里除了盐老鼠以外没有其它动物。
这里缺淡水、缺氧气。这里有些地方年平均降水量约为24.4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3587.8毫米,为降水量的142倍……
他们这帮年轻人被分到柴达木各个盐湖,住进了支在盐滩上随时都可能被风刮走、摇摇欲坠的小帐篷中……多少次大风过后,帐篷、锅,碗、瓢、盆、被子全刮没了,唯剩几十个抱成一团的汉子……
共有五个伙伴在戈壁滩中迷了路,几年后我们才找到他们的尸体,那尸体已被腌成“人千”。我们在盐滩中经常发现盐制做的黑色“人干”在戈壁滩中经常发现“木乃伊”……
“1960年那场饥荒,我们只吃盐巴、观音土饥。饿死了多少盐工呀!可是,只要有一口气,盐工们仍要争着上工的。后来,实在不行了,场长抽出部分盐工组织了打猎队。进山的途中,我就那么跟睁睁地看着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死在路上、泉边。待打到猎物回来看到工地上的盐工们已瘦得像脱了水,两边的胯骨割得胯骨上的肌肉血肉模糊,鲜血从工作裤浸出又顺着腿往丁流,晶莹的血一层一层凝固了成一棵一棵倒‘长’的血树。我这个硬汉子也忍不住哭了……”
老严讲着,一脸的漠然,仿佛那是一段几万年以前的历史。
我们来到了盐工们用十字镐在盐盖上开凿的沟槽盐田。
“只需在盐湖底挖上槽,槽里的盐就会自己‘长’起来,挖去结晶盐,槽中的盐又会‘长’起来,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又一茬,永远割不完……”
老严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柴达木盆地的盐湖中有碳酸盐、硫酸盐、硼酸盐、氯化物等近百种矿物和四十余种化学成份的湖表卤水及晶卤水。其分布呈明显的分区性。从盆地外围到中央,从硼锂矿向钾镁矿床过渡……
1937年,者严在茶尔汉盐湖——年产20万吨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修建美国汉森公司引进的两艘配套采盐船配套的1.8万千瓦自备火电厂。柱子一样粗的钢筋混凝土桩柱连向盐漠夯了八根,桩头都劈了,原来地基下面有一层厚厚的铁板沙。 “最后我们将长8米,直径500毫米的钢管用机械戳进地里,再用高压水枪将钢管内的沙石冲出来,然后注入鹅卵石,使鹅卵石在振动机的强烈震荡中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形成了能肩负万钧之力的鹅卵石桩柱——那铁板沙虽坚如磐石,在振动机的震荡中竟松散得没了一点儿凝聚力,主厂房就是建在这种碎石桩上……” 老严不再讲话,低头走在我前面。留给我一个孤独的背影,一个沉思的背影,古铜色的肩夹中汪了一汪汗水。
起风了,漠风从四面八方吹入戈壁。一时里千弦万调,干音万律在我心中四起,在旷野回荡。 “呼啸的风/伴我走过古老的荒漠/飘移的云/伴我浪迹天涯的追逐/眼前是苍茫/身后是沙丘/占铜色的股庞在骄阳下闪烁
“漫漫流沙/不断掩盖我的脚印/悠悠黄尘/不断揉碎我的幻觉/哪里是路/哪里是路/一个灵魂在沉闷天廊里徘徊”
那干百个合声仿佛是我的激情,我的创作灵感……
风声越紧, 一个坚定有力的在音胸合声中回荡:
“一步一步的跋涉/一串一串的血汗/一声一声的呼唤/一遍一遍的探索
“我辨认辨认这荒原本来的面目/我觅寻觅寻这戈壁生命的绿洲/我不悔不侮这人生路的选择/找抗挣抗挣着触摸每一寸冷落”。
风更紧,昏天黑地,沙子拍得脸生疼,我仿佛看见了那一个个在风中扭曲挣扎的男子汉。
“久远空旷/暴烈漠风/给了我石一样坚定的品格/给了海一样宽阔的胸廓/一行足迹/一首壮歌/我把深情献给荒漠……
“我是一片象征春天的绿叶/我是一缕相思情深的云朵……”
泪水,夺眶而出。那曾是盐工们一双双布满红丝的眸子涌出的泪水呀!
我终于谱出了这首词作者将兆忠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血泪写出的歌。我终于较准确地把握了词作者的情绪起伏。
哦1这琼花!这苦涩的结晶。
许是泪、许是汗,许是血……
许是希望的结晶、幻想的凝固,痛苦的演变……
回望,那海市蜃楼,仿佛在演示盐花的形成过程:那是七八干;可年的历史呵!先是一片浩瀚的大海,接着是向北飘来的印度板块,再接着是西马拉雅山脉隆起,海水退去,形成中部下陷低洼的封闭和半封闭向心汇水盆地,印度洋的暖流,河西走廊的季风被阻隔,盆地中的积水大量蒸发而渐渐干涸,留下一个晶莹透明的盐的世界……
那“幕布”上放映的像千万朵百合花开放的过程,那配乐恍惚就是我那起伏交错的千万个合声……
假作真时真也假
——青藏公路沿线采访散记
离开茶卡(蒙语,盐巴),过都兰(蒙语,白色的水),我们的车就进入沙漠,目的地是格尔木(蒙浯,江河汇聚的地方或盐泽)。
这一片寂静是黄色的、浩瀚无垠的。
沙漠上白色的反光似亿万条向天吐着信子、扭动着身躯的白色毒蛇。
开始不停地眨眼睛,两个眼海中捞出的平放在沙滩上的圆鱼,头对着头、嘴
对着嘴,绝望地一张一合,一合一张,发出极轻的“啪,啪”声。
唇开始发干,我便开始一层一层揭嘴上的皮,被人警告: “再揭嘴就没了!”一笑,唇又裂出几条口子,忙用手将嘴捏住,又惹得同伴们一阵大笑。
忽然,远方有一些白色的浪花向我们奔来,仿佛无数群狂奔的白马, “马群”越奔越庞大,“马群”的后面,蓝色的海水奔腾而来。 “马群”与大海奔到距我们约100米的地方倏忽不见了,又有新的“马群”与大海奔到距我们约100
米的地方又倏忽不见了……
渐渐地,四周都似有海水向我们涌来,且都与我们保持一段约100米的距离。都说是四个海市蜃楼。
那迷离的蜃气之上有无数幽深无比的彩圈儿从近向远飞跑着,像无数火车穿行于彩色水晶石修成的长长的隧道中,那“火车”消逝的远方,总似有那么一种不可言表的寂静。
细细地看“海”,却见波涛滚滚,海雾迷潆。一种只可感知的苍茫,一种只可体会的雄沙之中翻飞的枫叶儿。
海雾越来越浓,海鸥越飞越多,海浪越打越汹涌……
海在“咆哮”、云在奔腾,海鸥在搏击,一种气势扑天盖地而来。这么真实的场面中却听不到海的咆哮声、云的撞击声,海鸥的呜叫声,甚至听不到任何一种声音,这平静,便不仅仅是使人感到不对劲,而是一种神秘,一种恐怖,从四
方八面悄悄潜伏而来。
车在沙海中越走越小,人在沙海中越走越小。仿佛我独自划着一叶扁舟,在茫茫无际的孤独海上航行,前面似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航道,通向孤独海的深处,又似通向太极时那一片混沌,更似沿着古道通向生命的最里层。那航道像一个无限长的透明的牛角,为了前行,我一次又一次蜕皮;为了通向一道道生之重门,我一次又一次地扭曲自己……
不能不为生命尽头那一盏小小的、在海浪中出没的航标灯而深深地感动;不能不为茫茫沙漠中那一行寻求着的弯曲曲的细瘦瘦的足迹而深深地动情。
似乎真的在人海中航行了很远很远。
我想起了那支歌: “我驾着一只小船,飘泊在人生的海面,每时每刻都有风浪打来,海水呀为什么又苦又咸。嗨约哟嗨哟,嗨哟哟嗨哟,我阔。无数海鸥在海雾中翱翔,像无数片在漫漫流拼命地划哟,划哟……”
越往沙漠深处走,越发寂静,越发觉得不对劲,更多的神秘得令人恐怖的阴影潜伏到100米以外就隐遁了,却能感到它们蹑手蹑脚地向你袭来。仿佛有一种兆示: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既将发生。
回望同车的人们,一些淡蓝的烟雾萦绕在每一张脸上,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显得不真实,仿佛沉浸于一个谣传之中,又仿佛才戳穿了一个谎言,又仿佛在一个荒谬现实面前遐想……又仿佛等待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如果那事儿不发生,一
切就越发显得不对劲。
就在这会儿,一道绿色的屏障,从右边的 “大海”中浮出,屏障由无数青葱的树组成,树下是宛若明镜的水,水中映出摇曳生姿的树影,飘动着云影、鱼影、鸟影。
车中蓦然热闹起来,似是等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人们的脸上有窃喜、欣喜,欢喜……
左边的人统统站起身来挤在车厢走道儿上,将身子弯下,把脸对着右边的窗子,像一大丛秃枝被漠风吹了向一边倒的木麻黄。
“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一时里车厢里像放鞭炮,这里进出一个“真的!”那里跳出一个“假的!”
一响一响炸了很久。
“爆炸声”忽然停了,大家回过头来面面相觑,又“轰”地一声笑了。
唇又裂了,忙用手一撮,大家看了我的狼狈样子越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绿色的屏障依旧似真似假。
大家不再争论,只是以不同的姿态望着沙漠中绿色屏障的延伸。
人们的脸上都浸在一种梦寐般的光晕之中,仿佛看透了爱撒谎的大沙漠,平静地等待着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刻,又仿佛面对一个高明的撒谎者,为辨不出撒谎者所说的话的真伪而显出那么一种兴奋;更仿佛是自己所杜撰的故事被证实,而显出那么一种博大渊深的样子……人们的脸上似都显出宽松,似乎就是被捉弄一下也使旅行显得丰富多采,也使渐渐空虚了的心得到一种满足——沙漠太单调了,似乎人们觉得沙漠就是当有种真假不分的感觉才对味儿。
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心中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顽皮与一种孩子般的渴望,这种一会儿觉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会儿觉得一切都虚无飘缈的感觉很新鲜诱人,使我的嘴角不知不觉地也挂上了几丝儿‘玩世不恭”的微笑。
前方出现了几间土黄色房子。大家疑惑地相互望望,那一双双眸子里分明写着: “这房子是真的还是假的?”车子在房子前停了。大家又疑惑地相互望了望才下了车,望着那房子谁也不敢上前。越发觉得周围感觉不对味儿。这时,房子
里走出一个戴白布帽,黑皮肤,穿白衬衫的小伙子。大家又回头相互望了一下,那些目光中分明写着, “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小伙子笑笑,露出一口白牙,做出一个“请”的姿势。大家站着不动,谁也不敢接受这个或许是鬼魂、或许是外星人、或许是幻影,或许是魔怪的邀请。双方僵持住了。天地静得有交流音从四方鸣响。
我脑海中闪过在沙腹子看到的那围着风蚀残丘的八具木乃伊,闪过在雅丹地貌区域看到的三具已成为其地貌中无数“狮身人面像”中的三尊的一坐尸……忽觉土房边这些横七竖八的树是一个生死搏斗的宏大场面被人类活动空白期保存……
这时土房子的门帘被掀开了,一张张圆桌上围坐着给我们“开路”的青海作协主席朱奇老师、陈讽老师、河北作协的几位老师等。我们伙里不知谁指着朱奇老师说, “这也是假的!”“轰”一声“巨响”,我们全笑了。
那个幽幽的、怅怅的、郁郁的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人们一下子回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朵一朵“花”真真实实地开了。人们被沙漠“捉弄’得很开心,很满意,太阳恍惚一下子柔和了,沙漠也一下子与我们亲近了。
我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思忖着怎样问这几位戴白帽子的店主,那绿屏障是真的还是假的?望了望喝茶的同伴们,眼睛珠子溜来溜去,闪出特别的光采,知道每一个人都想搞清这问题的。我分明看到那幽蓝色的气氛又一丝一缕地慢慢爬上每一个人的脸。仿佛刚才有谁突然关闸将水截住使人们见了河底,而那闸又慢慢儿打开了,幽蓝的河水又弥漫了河床。
当几位戴白帽子的店主告诉我们那绿屏障是真的,是诺木洪农场所在地时,我们忍不住又笑了。趁人不在意时,我拧了拧自己的胳膀,感到一阵疼时,我忍不住心里又偷偷儿笑了。
可是笑完了,那种不真实感与时空错乱感又悄悄潜来,又有许多疑惑涌上心头。那幽蓝色的水似被击了两下,露出隐约的水底,又慢慢恢复了。心巾不由涌出一阵淡淡的苦涩。
以前的人是望了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以为是真的,跟了它走了一程又一程,以致……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沙漠之外的人们,却是见了真的以为是假的,在思维中绕了一圈又一圈却终也转不出来。
我们这些人90%是第一次到沙漠,可是我们都听到了太多太多关于“海市蜃楼”的传说,我们似乎都有了“经验”,我们似乎都形成了一种“看法”。而沙漠对我们的诱惑之中的一大部分不正是因了这些传说吗?
而这些纯朴的人们又是怎样生活于“传说”之中的呢?怎样工作于“传说”之中呢?尤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不由地想起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个介于商界的日子,不由地想起在特区在南海追寻的日子,不由地想起那叶飘泊的小舟上又剩我一个人时,当所有的风、所有的雨、所有的猜忌,误解都化为浊浪左右前后扑打而来时,我一遍又一遍唱过的
那首歌,
我驾着一只小船,飘泊在人生的海
面,每时每刻都有风浪打来,海水呵为什么又苦又成……
嗨哟哟嗨哟,嗨哟哟嗨哟,
我拼命地划哟划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