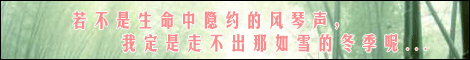朦胧恋师情
可能每…位少女都有过一段朦胧的恋师经历。因为青年教师是第一个有机会从一个高度如同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从天而降的异性。
但那只是一种朦胧的情怀。它飘乎而来飘乎而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轻轻淡淡的,似有似无的,带着少女时期特有的空灵。
而那个梦总不是一个少女的梦,而是那么多的少女一同做过的一个关于一个男教师的梦。真是奇迹,在青海时我看了女友今子写的《夺师》,更加了解了这种深藏在我们少女时光中的隐秘。可是过程。与结局却是那样的不同。
那时我刚上初中。班主任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开始并没有感到他有多么的英俊出色。他的个子1点78米左右,头发泛出浅粟色,短茬茬全是立着的,如沉在一个静电场中。脸如一个鸡蛋。整个神态如同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放大了几十倍。第一次见面给人一种十分深刻而难忘的便是
那怯生生的神韵。那嘴唇上真还有一圈如同孩子吃过奶的痕渍。整个的肌肤都是泛着红光如同是新生儿一股。走路似乎是只用脚尖,有一种不可以用语言形容的轻盈与敏捷。惟一让人心动的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无论如何他与我心里的白马王子相去甚远。
刚上初中我就进了学校宣传队。他是二二胡伴奏。每一次他都是静静地来静静地去,从不多说什么话。而每一次他说话之前居然还带着一抹羞涩。没等你听清他说的什么话他的脸倒先红了。
第一次多的接触是拉练时他是我们的带队。我们学校宣传队的五个小姑娘去塔尔寺拉练时照顾我们用车拉着我们。回来时让我们插入班级,参加拉练。那时我们都是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总是怕。可是无沦我们何时回望,凄迷无助中,他总是静静地望
着我们,总也善解人意地脸涨得通红,给人一种亲切的熟悉的什么。转过来我们又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一个,恍惚并没有离开家似的。
才走了几天我们许多人的脚上都打出大大小小的水泡。他教我们用一根头发从水泡中穿过去。他的动作准确而有力度,泡中水在头发穿过的那一瞬顺了头发涌流出来,既不痛又不痒,而他的脸却又红了。第二天我们脚上那些瘪下去的泡既不影响走路又不会如那撕破的泡一般流出鲜血。
他表现出的沉着与有耐心迷雾一般地环绕着我们,无声元息地陪伴着我们,似乎是一种极不真实的智慧。
在解决一个问题时他像一个大姑娘般腼腆羞怯。可是却是那样的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还有一种深深的悟性。而体育教师的轻捷也日渐显示出他内气充盈的英俊与萧洒。
他;不爱讲话,但给人的感觉总在观察事情,静静的却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浸透力、感悟力、感染力。他处理的事情一定没错。
渐渐地,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引起了女生的注意,他那举止微风的形态和与生俱来的羞涩都成了他的一种优点。渐渐地女生们开始议论他的一举一动,重复他说过的某一句话,窃议哪位女教师到他那去过了……而那时几乎我们班的每
一个女生都对他的一举一动感兴趣。话题绕来绕去又绕回他身上。总是有新的发现。只有我对此不以为然。总觉得与他我心里的白马王子相去甚远。
渐渐地,我们班的女生似乎都无法抗拒他身上的一种默默的浸透力。似乎他在那里以一种毅力做一种静功,那个笼罩着他的静电场把她们一个一个都吸附了进去。而男生们似乎更早地被他磁化。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终于,她们、他们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大的电场,我恍惚是惟一的一个游寓在那大电场以外的一个拗拗的小家伙。我依然我行我素,有时我与长得已如大姑娘的同学花同行,她放学前总是要找理由去看班主任。她在班主任老师的教师两
人宿舍里,我就在外面等。听到她在里面说笑,从不打算过去,也从不过去。这么多年。恍惚我还是站在门外,还是等着花的出来,还是听到里面的笑声在隐约地起伏。
那时班里的大女同学有事没事找他。而不论哪个女孩子去找他,他总是默默地看你说看你笑。看你—上演完你的节目然后目送你远去,那么一种远离这种喧哗的沉静。他对于女生的对他的关注从来不责备也不鼓励,只如一切与他无关一般任那些情感默默地生默默地去。就连某些女生的纠缠,他从来不批评什么,只是默默地观事态发展,我自岿然不动,拒你于。几米之外,仿佛他在那里静静地看岁月的云烟在自己的眼前上演。他让那些少女朦胧的梦从头做到了尾。醒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多了一种生命的珍藏。 或许正是我这种不听话,这种游离于众少女之外的拗,得到了他的赏识。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学什么?可是他为了提高我们的智力经常找来一些智力题让我们做。什么分油啦!过河啦!分地啦!问路啦!
比如:用四根火柴摆出一个“田”字;两根火柴摆出一个“口”字。比如十棵树栽五行每行四棵……
而每一次我都是第一个做出来。不久我发现我与班主任之间多了一种默契。每一次在他出了一道难题总是习惯地望望我有什么反映。而我总是有那么一种灵悟对于他发给我的每一个信息。每一次看谁先做出,他的目光也是总先投向我。那一次他看我又第一次做出他出的智力题,便走到我的座位上给我”—个人出了一道题:九棵树栽十行每行三棵。我又一次做出’厂这道让高中生、大学生都犯难的题。我感到从那以后,班主任对我更加地刮目相看。
那时工宣队、军宣队轮流进校。叫做“请进来走出去”。
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老师领了帮工人师傅与对面红一师的实习生进来,他让我站起来对那些人说:“这位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毛竹……”
而那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的这个野丫头不知道刚到哪里野过,脸被抹成一个花脸,衣服口袋都扯开了,衣服上几个大洞。我那样子真的不像班里的重点。可是他视而不见。他的确把我当成班上最重要的“人物”介绍给工宣队的“教
师”们与来实习的老师们的。“注其神而忘乎其形”。我感到他似乎在意的是我内在的什么。渐渐地,我感觉,他全身贯注感觉聆听的恍惚只有我一个人,其它学生对于他恍惚并不重要。
渐渐地,我这个游离的电子,那么真切地感到以他为中心那一个静电场在向我放电。可是我仍旧执拗地不肯加入。
让我的感情发生质变是他对那一次全班女生孤立我事件的处理。
那是初二下半学期,我也不明白班里的女生为什么要孤立我,原因似乎很复杂,这是一个需我不断破译的谜。好像主要是因了我知道的太多主要是指知道关于少女生理变化方面的事情。 孤立我的领头是班长杨秋玲,那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美丽姑娘。她会拉小提琴会打乒乓球。那时她带着平时与我好的女友们:李美英、阎兰萍、张香兰等,甚至带着这么多年一直与我相好的一些好友。那时我是班委中的文艺委员。
那时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女友L姐,她的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在身边,似乎是在狱中。她家成份也很高,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家就在我家楼上。她长得雅致高贵、秀眉秀眼的。我们在一起讲故事,在一起玩,她作为一个大姐姐看我发育到了快来例假的时候,而母亲又不在身边,就给我讲少女的生理变化,讲当怎样对付将来的“红色猛兽”,给我看她发育起来的乳房……而我看到周围的女友也正是十三四岁的青春期,也到了来例假时候。
就在这时对面中学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女孩子来例假不知道,结果血就顺了裤子流了下来,弄在教室地上。丢了人,女孩就要自杀,跳到湟水河里又被人救了起来。
想想那时真是杞人忧天,怕少女们丢丑,就如怕自己丢丑一般。结果就把L姐对我讲的自己都不太懂的一些话讲给了几个女生。那时我并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时我所在的学校宣传队的一个女孩居然能从哪个女孩的眼圈看出这个女孩子是不是正在来例假。然后这个女孩就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在她身边悄悄互捅耳语,观察她坐过的凳子上是不是留下红点跟在她身后看她走路是不是有些异样,看她是不是身上带有卫生纸……这个例假中的女孩稍不留意就给在大伙儿中留下笑柄。女孩们一个一个噤若寒蝉。
那时我们班一个不起眼的女生上课时撕了几张作业本上的纸举手请假出去,顷刻间她就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若是哪位女生今日体育课没上她立刻成了班里的焦点。
有一种神秘的东西笼罩着班集体,一种朦胧的羞涩笼罩着我们。还有一种恐怖在女生中神出鬼没。
“她今天倒楣了!”“她病了!”“来例假了!”准也不敢直说出一个“来月经了”仿佛那是一个潘多拉的魔匣子,谁都颤颤兢兢地绕开,谁也不敢打开。
而且每一次上体育课给来了例假的同学请假时我们女生的神情都是神秘莫测的。说来说去体育老师还不懂,便有一种红晕在女生的眉眼间悄悄传递,扑朔迷离。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女孩子是多么美丽。如果加上暗示性的语言男教师还是不懂,便有一种怨怅在女生的心里油然升起。现在想起来,那种怨怅同样美丽。而年轻男教师的每一句回问都会让我们女生在一起推测半天。
男生与女生之间有了秘密!男老师和女学生之间有秘密。天地间有一种奇异的萌动。而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傻乎乎地触动了这一根女生尤其敏感的弦,打开了那个装满魔鬼的匣子。
那时我们正好在下十里铺大队学农.杨秋玲带着那些少女在那边玩耍,她们叫着笑着跳着,李美英、阎蓝萍、张香兰在互相追逐……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面站着。众多少女的那一边阳光明媚,而我的这一边土包上几根冰草在阴风中瑟瑟缩缩。我看到一个蚂蚱冻死在馒头花丛中,一只扁担冻僵在冰草之上。而那些长长的冰草在风中起伏着张扬着我的孤独与我的无助……我从没有哪一刻如那一刻那么真切地记住每一位少女向我张扬的美丽,秋玲那微笑的甜美,美英那曲线的丰满,蓝萍那身影的健美,佚名那大辫子的飞动……由于欢乐由于跑跳由于笑闹由于得意,她们的身上热气腾腾……
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次事情更让我难堪与尴尬。
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孤立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漫漫长长的三个月。多么凄苦难捱的三个月呀!我感到整个的我摇摇欲坠。我心力交瘁。我快要崩溃了。对于一个少女,这是怎样残酷的一种精神折磨与精神摧残!
而那个环境不是在学校,我可以找其它班的女友玩。那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农村,而且我们还不跟农民一起劳动。
以前都是我甩别人,并不是有意的,只是一种本我的行为。我独来独往可是有那么多的人盼我的回来。而我每当在大自然中玩几天我就会回到孩子们中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甩的滋味儿。真是一种报应!
我含着泪背对她们,可是风却把她们的笑声真真切切地传给我。我感到老师与男生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形单影只的我,我恍惚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我恨不得挖个地隙钻进去。
泪水总也是在我的脸上结成薄冰,几缕头发总也是冰在我的眼睛上。
我如一只悒郁的孤雁,离群索居,孤独地在雪地上匍匐,拖着伤腿。
我总也是用雪将冻伤的手来回地擦。
那个镜头在我少女的生命中太重要了,以至于成了我终身难忘的一个镜头。
女生们当然不肯告诉班主任孤立我的原因,因为那事本来就是我们女生中的秘密。她们不告诉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话根本就说不出口,别说是对一个年轻的男教师就是对一个女教师也同样。她们不可能告诉男教师,我不可能告诉男教师。我们女生中的事情,谁也插不进手来的。我们都以为班主任也就不可能知道我的罪过。
我当时也意识到自己恶孽深重,这不是传播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后又传播黄毒吗?我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家庭成份又不好……本来就有被当成资产阶级小姐批斗的危险。而我平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不小心流露出的女性的柔性。这一次怎么忘了呢?
那样的话是可以说出口的吗?我自责!这种自戕对我伤害更重!孤独带给我一种深重的耻辱感。我感到整个的我轻飘如梦摇摇欲坠。
三个月终于过去了,这一次全班女生孤立我事件的处理结果让我们女生统统大吃了一惊。
班主任从不轻易表扬人的。可是那一次他表扬了。他说:“这一次三个月的学农尤其表现好的我要提一下!特别地提一下!那就是毛竹同学!”
不用他再说什么,感觉他身上传递出来的微妙的气场,杨秋玲只看了他一眼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李美英、阎蓝萍、等人似乎都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羞得无地自容,都一个一个伏下头。
本来似乎是天大的事情,几乎要一个少女付出生命的事情,可是他轻轻地说出一句话来,这句话一下子点在点子上,从而使天大的问题变得简单,使班里复杂的矛盾一下子迎刃而解。而他就这一点,杨的那一个派一下子就散了。班里又成了一个整体。只计一点不计其余。后来我才知道杨秋玲孤立我的同时还组织学生给学校几位优秀教师:数学老师郑章、音乐老师丁桂珍等人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后来的大字报是以杨个人的名誉贴出的。
他处理这个微妙问题的心理对于我是一个永远的谜。
我当时以为:女生们不好意思告诉班主任孤立我的真相,而他作为班主任对我的印象本就不错,因为不理解孤立的理由加上男人向来都是同情弱者,所以促使班主任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排斥班里已形成的那个博大的气场,对我更加信任更加器重。我总以为这里面有误解。这是男女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沟通障碍引起的误解。
而后来我从班主任目光中看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他似乎什么事情都知道。
先是生理卫生老师向我们宣布下一节课给讲“男女生殖系统”这一章,男生与女生分开到试验楼上。男老师给男生上,女老师给女生上。这是那些年从没有上过的教学内容。
我们抗议!不许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大喊大叫,又要造反。我们敲桌子踢凳子扔煤砖,教室里乱作一团。气得老师又叫又骂歇斯底里,可是不好使,班里更乱了。
就在我们准备把老师轰出去的当口,我们中的一位一回望,看到班主任老师不知何时已经进来不动声色地站在教室后面,忙大叫一声。我们一回头,先是慌乱了,后是老实了。
我们的班主任似乎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人,可是却对每一位同学都保持着一种深深的默契和与日俱增的威慑力。他的威望一日比一日高。
他走上讲台,目光炯炯有神地扫一遍,全班立刻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见相互的心跳。他示意生理卫生老师接着讲上课的要求。全班人屏息聆听,那乌烟瘴气的教室渐渐变得清澈透明.最后安静得连掉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他的身上真的带着一个透明的气场!有着一种灵魂中的撼动力!而他的头发似隐示气场的方向。
第二天,我们男生女生分开站成两队老老实实地进了两个试验室。进去前我看到生理卫生老师目光迷惘着散乱着,而回望我的班主任我发现他的目光是那样的笃定那样的沉着。这一瞬我恍惚觉得他更像一个谜。他对于女生孤立我事件中的详情真是不清楚还是一清二楚?他不动声色中卖的是什么药?真是微妙而又微妙。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不明白,那真是一个未婚的青年男老师处理问题的深度与力度?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而他怎么可能体察少女在生长发育期微妙的心理变化?这真是不易!由不得你不惊叹。他太知道照顾女生的自尊。他从没有批评过什么人,可是却让你从他的眼中那么真切地感觉到鼓励还是责备。
他一件事情处理得比一件事情精彩,使我一次一次对他刮目相看。使我感到了他悟人悟事的深度与厚度,使我拗拗的心底终于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
由于他一句轻轻的表扬,上初中后从来就是被大伙公认够三好学生条件但从没有当过三好学生的我那一学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后来,在他与第三任班主任郑章老师、校团委书记宋金兰老师等的共同努力下我这个背着重重“包袱”的“问
题少女”终于加入了这么多年一直想加入而不能加入的共青团,实现了我这个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少女多年的愿望。
在我被孤立的那些个凄迷无助的日子里我根没有想到这一次孤立的结果居然有利于我。
从那以后,他的身影一直伴着那个拗拗的少女很久很久。抑或,从开始到后来那个少女都没有搞清心里这种朦胧的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现想起来那时我不想当文艺委员想当学习委员,除了虚荣心作怪,除了想离外号“资产阶级小姐”远些跟潜意识中想通过交作业接近他是不是有关?跟这自己都搞不清的朦胧情感是不是有关?
感到自己还是不肯加入以他为中心的大气场,可是却那么真切地感到那个大气场以一种不可抗拒之势在吸我。那恍惚是一个朦胧的青春大气场,变幻着色彩在诱惑着我的加入。我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气场内外静静地感悟,细细地聆听一个年轻异性生命的律动。
后来有一个人给我看手相,说我12岁以前糊里糊涂的,到了12岁才开始蓦然聪明了的。让我由衷地叹服。是的,我是个属于大自然的孩子!一进到教室我就傻乎乎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走出混沌在古板的课堂上倏然开窍。一下子蹿成班里的学习尖子,可能与他有关。12岁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情:一个就是我由一个眼睛一单一双的野小子变成一个双眼皮的美丽少女;一个就是“本我”之外的那个我活过来了,我在课堂上变聪明了。
想起那段朦胧的情感,我不由地想起徐志摩的诗:
我悄悄地来/正如我悄悄地去/挥挥手/不带走一缕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