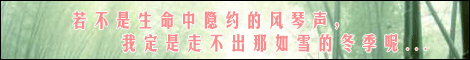毛竹小友:你好。
我刚从老家回来。上次我曾给你发过一次邮件,但没有成功。这次不知如何?
你写的那篇有关我的文章早已拜读。谢谢你对我的关心。里边的内容大致属实,有些细
节的出入也无妨。这类记忆式的文字,因叙述者和记述者
各自的心境、注意点等等的不同,常常会有不一致之处,没有必要予以统一。何况我本
是小人物小事情,无关大局,就更无纠正的必要。所以你写的那些有关高原人、事的文
章,也完全可以凭你自己所知道的去写,不必拘泥。这是你眼中的“人与事”,并非完
全的现实中的“人与事”,只要大体相似特别是精神上无大的违背处,即可。
随信附上我以前写的一篇同题材的小文,供参考。此文是一组文章中的一篇,其他三篇
发过,但这篇一直没有正式表。
我已经老而志衰,很少动笔。你正当写作旺盛之际,希望你多写,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来。
专此 即颂撰安! 士濂 12月28日
无法兑现的临终关怀
——《往事如烟》之四
沿着记忆的长廊,我回到了少年时代。那里,有一扇异常沉重的门扉。我得鼓足勇气才
能打开它。门扉的后面,我清楚地看见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沉沉地低垂着、微微地颤动
着。
那是我受刑前的父亲。
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层官吏,担任过禁烟督察处处长、税务局局长等职,1947年致仕
归里。解放前夕,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小叔去了台湾,我父亲和一直管家的大叔留在了老
家。虽然父亲有这种复杂的身份,但在刚解放那年他还能自由出入于杭州、上海一带,
到1950年秋末,随着枯黄的树叶纷纷落地,他也和另外一些敌特匪分子一样,被拘捕入
狱,先关押在区政府,后转送县监狱。开始,妈妈还以为是我家的剥削清算款“余粮
谷”尚未交清,就千方百计设法交款救人。后来才知道事情严重得多,绝非区区几十担
谷子能了事,就只能听天由命啦。
1951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村里传出来一个消息,第二天乡
上要召开公审大会,有批人犯要从县上押送过来。那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时
期,类似的公审大会常在较大的村镇举行,其结果大致都是被审者饮弹毙命。有平常较
要好的村里人就来告诉我家,明日的犯人中很可能有我父亲,让我们做些准备。大人们
除商议了些后事外,又提出最好家里去个人进会场看看,见上最后一面。可谁能进得这
森严的会场?村里的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有组织的队伍,我家的大人没有一
个挨得上边。唯一可能进会场去的只有我这个尚未成年的中学生。于是探视的重任就落
在了我肩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等候在学校去乡政府的路旁。我知道,每逢乡里有大型集会,学校
的军乐队都得参加。果然,这天也不例外。当敲着铜鼓吹着军号的队伍来到跟前时,我
蓦地从路边闯了进去,向带队的老师说明了原委,希望他们能带我进入会场。老师很通
情达理,答应让我随军乐队同去,但一再嘱咐我:“你可不能在里面哭喊。”我满口应
承下来。
大会在一个晒谷子用的大明堂里举行。原来空旷的场地上站满了人。临时搭就的主席台
上坐着几个军政干部。宣布开会后,先是奏乐,我的那些同学急忙吹打起来。接着是一
声威严的吆喝:“把犯人押上来!”于是,就有一队持枪荷弹的士兵,两人押一个从场
外将犯人带进会场。他们就在军乐队前经过。一个,又一个。突然,我看见了犯人队伍
中的父亲。入狱不到一百天时间,他的变化太大了:本来就已苍老的脸,现在又瘦削又
憔悴;加上满头的白发满脸的乱须,真是惨不忍睹。他被推搡着踉踉跄跄一闪而过,根
本不可能注意到混在军乐队中的我。
受公审的犯人被押在主席台的一侧,正好离军乐队不远。我能清楚地看见父亲。他一直
低着头,在我眼前晃动的也只是那一头白发。主席台上有人在宣读一个个犯人的罪状和
对他们的判决。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在这难得的瞬间抬起头来张望一下。这样他就可以见
到我,他的目光就能和我的目光相接。我是他最小的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能见到我对他
将是多大的安慰啊。但他没有抬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始终只是那一头白发。我想走过
去,轻轻地喊他一声。但我没敢举步。我想起了临来时老师的嘱咐,想起了我对老师的
承诺。我知道一个佩带红领巾的少年,要真在会场上喊叫那犯人的父亲,将会造成什么
样的后果。但是,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寄微弱
的希望于判决。我注意到前面的几次判决都是引用法律的某一条款,而随之传来的就是
无情的枪声。当宣布父亲的罪状并引用法律条款时,我希望不再是那一条。确实,条例
的引用与我所希冀的那样与前边有了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他与那些有血债的土匪有所区
别,因此判决也会不一样?我正暗自这么思忖,父亲已从主席台边被拎出去了。动作是
那样的快捷,我都来不及最后看他一眼,就听见了一记沉重的枪声……
作为反动阵营中的一个成员,作为新生政权的敌对分子,父亲的被处决是理所当然的
事。就是其时尚年幼的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在全校的大会上,我还曾在老师的动
员下上台揭发了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但令我久久不能释怀、至今还感到遗憾的是,在
我父亲临刑前我没能设法让他见我一面,没能最后叫他一声“爸爸”!
再也无法兑现了,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临终关怀。